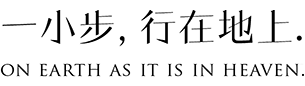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召命。
這樣說,會不會太宗教性?
換個說法,就是每個人都有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這件事不一定是很驚天地泣鬼神,但就是要由你去開始,由你去推動。
只要踏上了,就一發不可收拾。
回頭,發現自己的生命已奉上給這回事。
黃惠琼(琼姨)和大澳保育的故事,大概也是如此。
「有時,我都會想:為何自己會出錢出力,每個月交6000元租,開間民間博物館,打風還要拖地收拾搬東西。其實我在家裏晃著腳,聽聽音樂也不錯吧?」她笑笑說,「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大概這是上帝給我的工作吧?」(看另文 大澳文化工作室:元祖級社區故事館)
這也可以理解為天注定,或是緣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琼姨在大澳生活了57年,是很普通的水鄉女子:1958年出生,讀書至中三輟學,出來工作幫補家計,做過幼稚園老師,後來跟做公務員的先生結婚,成為全職家庭主婦,24歲生下了第一個兒子。
「如果說有什麼過人之處,我會說,保育大澳真的是我從年輕開始就有的使命。加上我有上帝給我的勇氣和勇敢,嗯。」她說,頓了頓。
「如果無勇氣呢,好難做……大澳是個地方細,人人相識的一個社區,鄰里關係密切就會有壓力囉。我每次搞社區工作,我呀爸畀人鬧、我呀媽又畀人鬧、我呀哥又畀人鬧、我呀嫂又畀人鬧,即係合家都畀人鬧。我以前面皮好薄,好易哭,這廿年來都訓練多了。」
琼姨第一次搞社區工作,就是做逆權師奶。那是1982年,她24歲,生下大兒子不久。
為八戶人爭取水電的逆權師奶
他們當時住在鹽田壆村,離大澳最熱鬧的永安街,不到兩分鐘路程。這村由百多年前的鶴佬人建,他們在鹽田附近,以茅屋和木屋臨時安家。「1958年,我爸爸來到大澳的時候,他的朋友就讓了這茅屋給我們住。」由50年代住到80年代,連孫子都有了,這條村8戶人家卻一直沒水沒電。
最荒謬的是,其實所有輸水管、高壓電線都在鹽田壆村頭上經過,但水務局、電力公司就偏偏不幫他們做工程,減低水壓和電壓入屋。琼姨跟村民1982年開始不斷向政府爭取,3個月後水務局終於來裝水喉。「但中華電力公司一直遲遲不回應,後來說要我們每戶夾12,000元才可以裝一個減壓站 —— 你知道嗎,那時我做全職幼稚園老師,人工才1,200元。我當然是不肯讓步,怎可以欺壓經濟落後的人?」
一個發電站,爭取足足三年,中電才終於為他們安裝。「人類1969年上月球,但我家是1985年才有電呢!」琼姨笑着說,「但這個事件讓我知道,有志者事竟成,而且當你說愛大澳、愛社區,不能只是說說,是要有所行動的。」
做社區營造,常常強調「愛社區」,但到底這愛是怎樣?
有時,最基本的,只不過是希望讓自己和鄰舍,都生活得安樂舒服點。
這是投身社區工作最重要的動力。
不然,就是因為你與社區的緊密感情,發現到它的獨特之處,很渴望保留下來。因為你知道,世界上將找不到另一個能取代的的地方。就像琼姨與大壆的持續抗爭。
一次又一次以為自己要完成使命,卻又一次一次的落空了。
那條乾隆留下來的大壆
「大壆」是指鹽田壆村看出去,從前建來保護大澳鹽田的一條古老堤壆。自從60年代起,大澳的曬鹽業式微,政府就不再維修大壆,鄉事委員會亦不願花錢在此。80年代,魚塘挖泥工程加劇了大壆的失修。後來颱風吹襲,更令大壆出現缺口。
「我從小到大都在這大壆看日落,我眼裏的大澳景色不能沒有它。」琼姨說,「它是一項保護民生的工程,是它保護像我們這些在岸邊的民居。」大壆的議題開始在居民中間醞釀、發酵,1988年琼姨意外發現了關於大壆的歷史証據。
有時也真不得不相信「命運」。
「那是天后誕,我跟母親去天后廟時,無意中發現廟內有碑文,寫着『護鹽圍追乾隆之瑞環繞太平平安之街』,一問廟祝,才知道就是原來是家對出的這條堤壆。」碑文証明,大壆原來有超過200年歷史,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發現。瓊姨把這個消息告訴區議員和鄉委會,誰知給他們冷待。
「我不甘心啊,這是我們社區的重要資產,是屬於大澳,也屬於香港的。」這個師奶,終於決定走上街頭。「我由幼稚園搬了一張很小的寫字枱,放在横水渡的入口,開始了(保護大壆)簽名運動,我是第一個在大澳以家庭主婦的身份發起簽名運動的人。」
在這裏必需強調,在港英政府年代,要收集簽名申訴,是很嚴謹的。簽名後面,必需有姓名和身分證號碼,且要核對清楚,才能上繳。「大澳人都把身分證藏得很埋的,因為不見了,就要來回五小時出去市區補領,所以簽名運動,對大家來說,都是不容易的。」
除了搞簽名,還要出中環行政申訴署見議員,琼姨找了當時立法局唯一一個,亦是香港第一個反對立《公安條例》的陳鑑泉議員申訴這事。早一天更約了中外記者們,開一個記者會。真想像不到一位師奶,怎去做這麼多事情。「那一年開始,記者就認識我,大概他們對於一個師奶願意花五小時來回去保護一條石壆,覺得很好奇吧。」
那後來石壆怎了?
「陳鑑泉聽了我們說,(代表立法局)跟我們簽了一份文件,要求政府在大澳沒其他工程時,必須先修緝大壆。但因為他之前反對《公安條例》,下屆立法局他不再獲得委任,政府就沒有繼續跟進。」以為成功,誰知落空。
硬淨的琼姨決定自己得閒去維修,又試過發起由學生、福音戒毒的年輕人一起修石壆,被大澳人嘲笑是「愚公移山」。1993年,索性自嘲,辦了個「搶修大壆之愚公移山大行動」,聯合學生、青年人和外頭的老師,一同加固。「我清楚記得當我用大聲公,向學生講大壆的故事時,我哭得好厲害。」
付出這麼多心血、時間和精力,結果又一次不如人算。
1993年的夏天,至少來了七個颱風,復修了的很快又被捲走。最後一次颱風甚至把幾年以來的心血都抹去了。
社區抗爭,是一個過程
「我記得,我坐在堤壆望天說:這個世界有沒有耶穌和神啊?我只希望用人力去修好這堤壆。從前二百多年前造了這個堤壆,現在我都只是想用三年修理好這個堤壆,為何會變到現在這個境地呢?而腦海中忽然出現兩個字,你們猜一下是什麼字?」
堅持?努力?繼續?
「當時我想到兩個字,叫做『過程』。」她說。
「我在搶修堤壆的時候過程備受居民壓力,說我想出風頭,但我不惜犧牲人力物力,不管風雨,就連另一半也阻止不了我。但最後我明白了一件事,我沒有King Kong的力氣,也沒有李嘉誠的財力;但搶修堤壆已經帶出了『關心社區、關心人』的信息,這才是重要,所以就立即跑回家跟老公說!」後來琼姨跟當時的記者朋友說,如果政府修緝,她當然支持,有人願意私人出資,她也願意再出力,但她真的盡了力,要放下了。
這個路向,若現在提出來,很容易被罵為「左膠」、「沒有成果就退卻」。
但當放回琼姨超過三十年的社區營造歷史線,卻會發現那真的是一個過程。
做個昂首向前的改革者
大壆之後,琼姨出版了三本大澳地區誌,辦了香港的第一間社區故事館「大澳文化工作室」。她和大澳的社區故事,比她原本的傳得更遠更廣。
30年來,沒薪水、沒勛章,就只有每個月定期要交租,或是從口袋裏拿錢印書,保育自己成長的地方。瓊姨認為可以做的她都做了,對這個社區已沒有遺憾。「最不好意思的,是搞到自己屋企人。」因為反對盲目把大澳改造成為外國一樣的景點,全家被人指點、當街被人罵,說:「你搞到大澳連屎都無得食!」2000年,她反對在大澳的淺灘建漁船停泊區,有居民衝入文化工作室,打她的兒子。「哥哥被人罵,不還口;阿仔被人打,不還手。真的好慘!但這代表他們是明白我在做什麼的。我是很感恩的,若不是他們,我怎可以做下去?」
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做社區營造,跟街坊講發展願景,就要有心理準備面這樣的困難和壓力。琼姨的建議是:「你要挺起胸膛,我走在大澳街上,或在踏單車都會突然被人截停,必需立即下車,給別人責罵一頓,然後處之泰然地離去。做社區工作,是要心理質素需很高,否則不能抬起頭來。就像當年耶穌被釘上十架,身旁也有許多人不明白。」
「慢慢來吧,社區就是細水長流的。」琼姨說,「因為根本急不來。」
這是一個老社區營造者的建議。「所以,後生仔,唔好吓吓都刀仔拮大脾,有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大澳不也是這樣嗎?以前人人都說大澳慢,沒發展空間,現在處處發展了,單一化了,大澳卻仍是一個可持續的社區。人生有限,盡力而為,有種平常心就好。」
這位社區營造「老江湖」看的時間線,真的很長很長。
(全文完)
text/ dydy
transcript/ haha
photo/ andy wong + chow ngash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惠琼作品集
《大澳水鄉的變遷--風、土、人、情二三事》 ,中英對照,香港,2000年
《澳水靈山》,香港:大澳文化工作室,2004年
《但願人長久》,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3年
繼續閱讀 大澳文化工作室:元祖級社區故事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