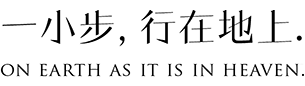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前言】轉眼《一小步》來到第5個年頭。採訪過的社區行動者,幾乎都成了朋友(Facebook’s Friend也算啦!)。這一兩年因着政治氣氛變化,我們觀察到行動者的處境也出現很大變化,有退下、有上前,有掙扎、有篤定;幾年一晃,行動者的臉孔改變了,行動形式也有更大的轉化。
2018年伊始,《一小步》很想跟這些行動者朋友吃一頓飯、飲一餐茶,增一下肥(誤)……其實是想見見這些朋友,聆聽他們的新年計劃,不讓他們獨自抱頭;因為《一小步》的編輯們沒有什麼長處,就是喜歡透過跟人連結。
不如就透過飲飲食食,讓我們聽聽行動者對社區的新春願望。
*這次與「與社區人食餐飯」專題,《一小步》將會跟四組社區行動者對談,也請來Trial and Error Lab 駐場伴伙Fionsay為他們逐一繪畫人像,向這幾位低調到不想拍照的行動者致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一年,希望每個人放下偏見,闔上眼,試試走一段路;
用心感受風是怎樣吹過、花是怎樣綻放。」
@Fishing Tsoi,視障人士攝影團隊「盲蹤踪」創辦者之一。

當生命出現一羣有趣伙伴
留一頭爽朗短髮的Fishing,大學畢業才兩三年。我們認識,源自她參與一個為少數族裔婦女翻譯的羣組 Translate for her ,她以核心成員身分接受訪問;後來知道Fishing在社福界當前線工作,也是生命教育義工、又是青年媒體的義務編輯。她同時喜歡到不同公民團體的講座學習,我們往後常在活動碰面,閒聊社區種種,於是就成了朋友。
2017年初,精力無盡的她,竟還創辦了「盲蹤踪」,跟視障朋友一起舉行攝影活動和展覽的組織。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發起的公民組織,從前她都只是參加別人的行動;所以這回春天的「一小步飯局」(哈哈),就圍繞她與「盲蹤踪」。「這不是一早計劃定的,只是機緣巧合遇上視障朋友,很喜歡跟他們一起拍攝,心動就不如行動呀!」
2016年底,Fishing跟5位朋友籌備於翌年4月,一起去斯里蘭卡旅遊。但他們也不甘於只是做遊客。「我們在旅程中安排了一次義工服務,去當地一個盲人組織,把舊相機與攝影技術分享。」於是出發前,他們特地向香港4位熱愛攝影的視障人士取經。
「我們10人愈交流,愈覺得盲人攝影有趣,也很有意思;就說笑我們(這個羣體)要叫做『盲蹤踪』,有哂隊名,很有士氣似的!」
幾位熱血的健視年輕人,就帶着視障人士授予的技術,於去年4月到斯里蘭卡當義工。Fishing自己也在旅程中嘗試蒙眼「盲攝」,「我由健視朋友帶路,他們用言語把四周的環境描述,然後我透過想像和感覺拍些照片。當地同行的部分視障朋友仍擁一定的視力,也能辨別有限的光暗與色彩,他們人生首次拿起相機攝影,居然拍得很不錯,有漂亮的構圖和豐富的色彩;我蒙眼拍的照片,有些卻是一團糟呢!」

Fishing(蒙眼者)於2017年4月與團隊來到斯里蘭卡西南面的加勒古城進行盲攝,體驗視障朋友的視角。(圖:盲蹤踪)
Fishing說,那次「盲攝」是她心眼的啓蒙,「有時,即使我們眼睛能看見,也不代表我們有用心感受世界的美麗;但視障朋友,雖看不見或看不清,卻能用心去拍攝,呈現他們對世界的感受。」
她回港後梳理這次經歷,「我以為自己常在社區為基層倡議政策,就很明白弱勢。經歷那次『盲攝』之後,我認為我不單可以為弱勢人士爭取權益,也可以辦一些活動,與他們一起,在比較平等互信的狀態下,去玩、去發掘世界 —— 或者,這將會是更有力地去改變弱勢狀況的行動?」
旅程完結,這「盲蹤踪」小隊正式坐下來,構思在香港共同辦一些盲攝活動的可能性,「我們嘗試先做些小活動,在市區和郊外舉行幾次盲攝活動,後來又做多一點,把視障人士拍攝的相片印成凸字明信片,聯絡不同市集去擺檔售賣。」
神奇地他們開始得到幾個知名品牌支持,而義賣捐款也可用作支援香港的視障人士組織,「後來我們更讓視障攝影者收到版稅,然後今年1月竟能跟視障人士去台中進行盲攝,3月初更將有大型相展……就像做夢一般,沒想過『盲蹤踪』小隊會走得這樣遠。」
由看似即興的行動,配合隨遇而安的經程,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可持續運作的組織。這聽起來似乎容易,但背後有海量的聯絡和籌備工作,極其辛勞。為什麼不選擇只做一次的「社會實驗」就算?
「其實很純粹地,當盲攝活動開始了,就會有人問下次何時再舉行。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商業合作,而是健視與視障朋友已建立了真實的生命交流。」
團隊成立只一年多,還有不少磨合,但大家都在努力學習如何理解對方需要。「視障與健視朋友一起去商量和策劃,彼此都有不理解的地方,例如健視朋友想舉行很多分享會,但視障朋友會坦言,他們有些在做較基層的工作如按摩師,上班時間很長,很難抽空。」

每張凸字明信片,都是一位視障人士的作品,也是他們的故事,每次擺市集都很受歡迎。(圖:盲蹤踪)
由行動參與者變成營運者
這年Fishing跟團隊一起成長,她由社區行動的參與者,變成組織者以至營運者,要顧及的事情是更大、更多。
因為「盲蹤踪」完全沒有經費,舉辦相展因牽涉印刷及場地,需要資金支持,Fishing負責把「盲蹤踪」受助者的需要,翻譯成不同的資助申請文件,花了她下班後的許多個深夜,捱出一雙黑眼圈。「各式各樣的Funding(資助)也有,由幾萬至十萬都有,只要是有創意、幫助弱勢社羣、兒童或低收入家庭都可申請。」
錢,總是有的。問題是如何讓對方覺得你符合他們的條件。所以填寫資助申請表得花上很多時間和心力,交待各種詳情,用不同的表達的手法,吸引對方的注意。「所以搞活動、相展即使困難重重,但也不及寫Funding申請的疲於奔命啊!」她抱着頭說,「這也是今時今日許多組織者的困難,在向社區募捐經費以外,只能不停花時間申請Funding。」
另一種疲倦,是Fishing累積了一些前線行動者的疲累,「我覺得自從香港人經歷過雨傘運動,大家對於身分及生活的危機感愈來愈大,積累了許多燥動,失卻彼此明白和擁抱異見的空間。」
好像這幾年她參與不少公民團體,常要跟人解釋「盲蹤踪」以至其他社區行動,又要進行不少討論;當別人冷漠地質疑「依家搞咁多嘢都唔會有用」、「盲人睇唔到嘢又點影相」又或「攝影幫唔到視障人士維生」時,即使她一笑置之,又或嘗試耐心解說,但這些香港人普遍的懷疑論與犬儒主義,還是讓她不快。「隱隱覺得這些比寫Funding、搞活動更令心身拉扯,但我不明白為什麼。」
直至一次,她跟其他搞行動的朋友參與禪修營,「那幾天,赤裸地面對內心的憤怒和眼淚,我嘗試坦坦白白問自己:『你為什麼不快樂?社會哪些狀態令你最不高興?』」營會有許多安靜時間,終於,「我記起內心深處最重視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價值,所以當看到弱勢在社會不公平的狀況,心裏就很難受;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即使疲累、傷心以至憤怒,這幾年還是不放棄參與公民社會。」
當初衷被喚回,渴望被提醒,「我好像明白了一些東西,我是最希望社會更平等,弱勢被看見。我想我要學習無論面對什麼人,不需再解釋我在拯救弱勢 —— 我只是想人活得更有尊嚴。」她微笑道,那次之後,開始再有力量走下去。

「盲蹤踪」也常會舉辦活動,給大小朋友嘗試了解視障人士的視野,透過體驗盲攝、聽實景聲音發現感官帶來的不同可能。(圖:盲蹤踪)
但願你也能闔上眼
2018年,Fishing有許多願望,包括「盲蹤踪」的種種新計劃的落實,例如3月10日將要舉行視障人士相展(詳情請看這裏);但她還有一個願望,想邀請大家一起做:「我想人人都嘗試一次盲攝,做一陣子視障人士。」這,會很困難嗎?「不,盲遊只是蒙眼,又或合上眼,用心靈去走一段路就是。感受風是怎樣吹過、想像花是怎樣綻放、經過的人是什麼樣子……」
去年第一次盲遊,就改變了她,「我當然想人人都支持『盲蹤踪』,但更希望你能真切感受這羣看不見的朋友,他們如何生活,那就想到如何為他們行下一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社區人食餐飯」專題並不就此完結,我們已把Fionsay的畫裝裱好送給行動者。願Fishing在寫Funding累了時,抬頭看看畫像中,那個用心靈去攝影的自己。


(全文完)
Illustration by Fionsay
Text by Gi
Edit by Dyd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社區人食餐飯】專題:
1. 盲蹤踪
2. 走杯Go Cup
3. 灣仔廣義
4. 街坊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