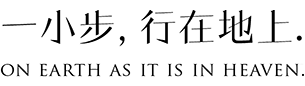要談「種族共融」這議題,在香港這個號稱「亞洲國際城市」(Asia’s World City)的地方,是那麼尷尬又彆扭。
我們作為一個「國際都會」的市民,理應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匯聚」,對不同文化國籍抱有好奇和包容。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少有與不同文化國籍的朋友溝通;更甚是,沒有接觸這些不同族裔的朋友的動機。(注意注意,我們說的是真正與他們共同生活,面對面的接觸,而不是只由劇集、新聞、吃多國美食等等的「接觸」啊!)而且,我們對於種族與階級的偏見是如此根深柢固:膚色略深的朋友,我們就視之為惹事生非的朋黨、非法勞工,叫自己與他們保持距離,容讓誤解、歧視和恐懼,繼續延展紮根。
香港的華人佔94%,不論在語言、生活習俗或教育政策上,社會幾乎全以華人文化為核心;但其實只要我們張開眼睛,就會發現少數族裔朋友一直在我們身邊。
跟他們一起坐巴士。
與他們一起在公園享受陽光。
小朋友跟他們一起上學。
在路上與他們擦肩走過。
「他們」,其實是「我們」一分子,是我們的鄰舍。
在香港出生、甚至祖輩比「我們」的爺爺嫲嫲更早移民來港的「他們」,誰更可稱得上是「香港人」?
在未來幾篇「一小步」故事,我們將會跟幾個由華人與少數族裔朋友(主要是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共同合作的單位對談,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創意的點子,營造華人與少數族裔朋友互相認識的平台,並打破人們對少數族裔的固有印像,努力讓兩者成為友好而平等的鄰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融館」外的屏麗徑日常風景之一:許多巴基斯坦少年聚集。(圖:共融館)
對異國街坊從不解到明白
週五下午,港鐵葵興站附近的屏麗徑小區,零零星星聚集了幾夥街坊。巴基斯坦少年湊到花叢邊嬉笑,年長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大叔,與中國人伯伯,坐到不同的長椅,又或到清真餐廳和五金舖門前,各自跟族人談天。當時鐘踏進一點半,穆斯林陸續走進一幢大廈二樓的清真寺祈禱。小區剩下華人老伯,幾個剛買餸回家的婦女,以及幾個巴基斯坦和華人幼童;孩子一同走到一個叫「共融館」地舖玩耍、做功課。
誦經、禱告、吃咖喱、打牙骹、買餸、孩童玩樂,就是屏麗徑小區每天的風景。
「我搬進這區三年,當時只貪這裏的房間四正,租金也負擔得來,卻從沒想過會跟巴基斯坦人做鄰居,真的!」年輕的全職母親阿Ling,懷裏是兩歲的兒子初初。初初還未上學,每天中午都會到共融館玩,今天剛玩飽,未及回家便睡着了。

屏麗徑街坊阿Ling在共融館認識了不少巴基斯坦人,成為左鄰右舍。
「初初搬來,我發現我家樓上每天就像播卡啦OK般,總有人在唱歌,後來才知道其中一個單位是清真寺,每天某幾個時段樓梯就塞滿去祈禱的巴基斯坦男人。而隔鄰單位又是巴基斯坦人,日日煮咖喱。有時出入會四目交投,但因他們身形魁梧,令我有少少驚。」她尷尬地笑說,以前不會分辨鄰居是什麼人 ,只一味說是南亞裔 —— 其實葵青區約有超過2,000名巴基斯坦居民,屏麗徑的少數族裔亦以巴基斯坦人為主(也有少數印度、尼泊爾人士),「南亞裔」一詞並不足以形容他們的獨特性。「如果不是有共融館,我不會有機會認識巴基斯坦人,並成為我和兒子的朋友呢!」
共融館,不是咖啡館、麻雀館,也非社區中心;它是2014年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獲巿區更新基金資助後,於屏麗徑設立的一個生活館,透過實體空間,讓來自不同種族而又天天碰面的街坊交流。這些交流,包括展覽、導賞團、工作坊和分享會等,「我是兩年前發現共融館的,先是我的丈夫參加這裏的南亞音樂分享會,慢慢他也叫我多來參加活動。」
阿Ling在此不知不覺地跟從來不打招的街坊交流,「起初見到共融館門口有巴基斯坦人跟我Say Hi,我有點不知所措,但這裏有華人也有巴基斯坦員工,我想也很安全,於是開始敢於回應,例如也Say Hi,問句『食飯未呀』。」

屏麗徑另一日常風景,是經常可見少數族裔與華人孩子一起玩耍。而圖中經翻新的木桌椅也來自共融館的。(圖:共融館)
阿Ling誕下兒子後,更多地與這些膚色跟自己不同的鄰居交流,「平日會帶初初來玩啦,後來跟廣東話很流利的館長文叔叔,還有其他巴基斯坦爸爸交流湊仔經,知道他們教育孩子的想法比較自由,例如不想他們太早學寫字,覺得生活技能比知識更重。」從前她又誤會南亞裔小孩特別活潑,後來才明白這些異國孩子更懂事,「他們不會像初初那樣,不知道玩得太過份會發生危險;大哥哥姐姐也很會照顧小孩,我也從中學會調整自己的育兒方式啊!」
因為視野的開闊,才能彼此欣賞,這是阿Ling沒想過的,也是共融館設立的初衷 —— 讓不同種族的朋友於同一天空下,有一個廣闊的交流空間,拉近文化差異,把誤會、偏見都一一挪開。

阿文是共融館館長,由外交大使、文化以至福利專員等等職務也由他負責呢!
由巴基斯坦人當萬事通
阿Ling口中的文叔叔,是巴基斯坦裔的Minhas Rashand(人稱阿文),他是共融館館長,也是員工之中唯一的外藉人士。阿文自9歲來港,居於葵涌,自小對於偏見很有經驗。「我們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每日要祈禱五次,一般老闆就未必明白。又好像去租屋,地產經紀明明已跟業主談好租金,見面時知見你是巴基斯坦人,即耍手擰頭說已租給別人。」
其實,跟阿文一起,你絕對不覺得自己在跟外國人談天。他完全沒有口音,新聞、市井俚語也瞭如指掌,而且還有很多爛Gag,「我以前做哪行?看更、小販、五金等等,還試過『炒嘢』。」炒菜?「就是炒股票啦!」「我怎麼會來到共融館?因為有少少能力啦!」係咪因為靚仔?「咁我應該去選港男喎!」我們都笑破肚皮了。
但談到純粹因膚色而被歧視,他不禁皺起眉頭,「我們好多兄弟的工作能力明明跟中國人一樣,甚至懂四、五種語言,但就因為外表有點不同,又或中文沒那麼好,人家就不請你,又或把人工壓低,很不公平。」聽着他用流利的廣東話訴說着同鄉的苦況,我們身為華人,感覺尷尬又抱歉。
但阿文自言比較幸運,一直不視自己是異鄉人,也不算有太多被歧視的經歷,「我朋友中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同鄉,波友也多是香港人,工作都算OK啦!」自數年前麥理浩夫人中心在葵涌開展少數族裔小組,他就幫忙做義工,後來成立共融館,他也順理成章當全職員工,成為共融館的萬事通。

一名滿臉愁容的大叔(右)來到找阿文(左)查詢申請公屋程序。
採訪這天,他一直忙於在屏麗徑跟少數族裔朋友了解近況,幫他們找工作、轉介政府部門等。甫回到共融館坐下,又有社工帶着一位大叔到來找他當翻譯,查詢如何填寫公屋申請表格;然後再有學校老師致電,問他為何學生要返巴基斯坦鄉下一個多月那麼久。他幾乎沒有一刻安歇。到週未週日,他更化身為導賞員,帶領華裔青年人和街坊遊逛屏麗徑、清真寺、南亞小店等。「香港人比較慢熱,那我就主動一些,叫他們放膽問;因為我們比較熱情,似鬼佬性格,哈哈。」
他覺得,共融館的最大用處,是能夠打開門,讓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願意走進來分享生活困難;「他們要面子,但當你能跟他們建立關係,慢慢就能為他們解困。同樣,因為有了這個地方,中國人也能有平台了解身邊少數族裔的處境。」他攤攤手,笑道:「其實我沒幹什麼,只是做了巴基斯坦人與華人之間的橋樑而已。跟華人交流,就用香港人的思維;跟同鄉談天,則代入他們的想法;這就是雙重人格囉!」

阿文(圖左)在導賞團中,正帶領參加者到屏麗徑的清真餐廳認識巴基斯坦菜式。(圖:共融館)
由社區需要出發
或許正如共融館的組織幹事徐斯筠所言,因為有一個真正的少數族裔同事阿文,再加上實體的空間,才能令兩地的文化有了交匯點,把文化誤會變成「長知識」。「我記得初來工作,要探訪對面那大廈的清真寺教長。那裏平日不許女生進去,但參觀、探訪則例外。那次明明覺得那教長人很好,對答也很有禮,但怎麼完全不與我眼神接觸?難道不喜歡我?」後來向阿文請教,才知道穆斯林不直視女生,是代表尊重。
我們日常生活也正正因着對少數族裔大大小小的誤會,讓誤解的雪球愈滾愈大,彼此產生鴻溝。「談到女性,你又有發現共融館很少巴基斯坦婦女來嗎?」對啊,她們像是很神秘,只能看到面紗遮掩下的大眼睛。「阿文解釋,原來她們因宗教理由,不能跟陌生男士身處同一場合,加上巴基斯坦人覺得女生像珠寶般珍貴,不能隨便被注視;所以我們為她們搞活動時,要請阿文暫時離開,又用布圍住玻璃大門,甚至最後要移師到她們的家,完全要尊重她們的文化。」

徐斯筠在共融館曾遇上不少文化差異誤會,例如曾送麥嘜給巴基斯坦人而被拒絕,你猜到原因嗎?
這些真實的相處經驗,是書本理論和新聞不能給予的,也正是共融館獨特之處,「我們不是社區中心,沒有太多agenda ,平日打開大門,社區發生什麼事,我們就參與。最常見是少數族裔的朋友找我們翻譯、華裔街坊來讓孩子問功課又或托管;同時又不少人到來參觀。至於活動也是有機地舉行,由社區需要出發,例如知道有人想看到電影,就問大家想看什麼,然後做社區放映;有巴基斯坦街坊會造枱燈,那我們又搞工作坊。」當然還有恆常舉行的社區導賞團和墟市。
起初「共融館」成立,卻曾給社區的華人街坊質疑道,資源怎麼分給「外地人」,「這些聲音我們都會聆聽,因我們不只服務少數族裔,也不是傳統那種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的社區中心。一方面我們讓少數族裔明白本地文化,投入香港生活;同時也拉闊作為大多數居民的華人,對於社區的想像,讓大家知道自己居住的地區有這麼多異國文化,社區也可以很好玩。」
就像共融館門前的公共空間,雖然只有約一千呎,但他們進行了花圃美化工程,種植植物,又請街坊一起把桌椅和車軚翻新,並把書本放到這裏,「即使放幾株怕醜草,不同種族的家長已會帶小朋友來認識和觸摸,街坊也多了在社區停駐的機會。因為這條街屬於大家,無分哪個族裔使用嘛!」
或者,我們應撫心自問,身為香港大多數的華人,視野是否有想像般國際化嗎?「我們口口聲聲說香港是多元文化的社會,但試問從小到大的經驗,又有多少跟少數族裔人士交集的片段?」

用揮春形式把多元鄰舍如此生鬼地描繪,也就是文化共融了。(圖:共融館)
當媒體和成見把他們塑造成看不見,甚至是不受歡迎的羣體;我們的確忘了,他們是香港多元社會的重要一員。
「有了共融館,大家便可從一句『Hi』 開始,嘗試與自己不同種族的人相交,」斯筠希望,「若大家從葵涌這裏回家,也把一句『Hi』帶到自己的社區,整個城市離真正的多元和共融便不遠矣。」
這天跟阿文談笑風生過後,我也嘗試跟辦公室附近那南亞小店的印度老闆聊天,向他買些香料,並請教烹煮咖喱之道; 如此輕易就交了一個社區的新朋友。

共融館的3位成員徐斯筠(左)、阿文(中)和石仔(右),努力營造一個真實的社交平台來讓少數族裔與華人街坊交流。
(全文完)
Text by Gi
Edit by Dy
Photo by And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為少數族裔的好鄰居」專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