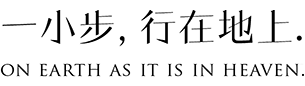由錦田,土瓜灣,到觀塘;一步又一步,我們從藝術手法開始,到開舖建立故事館等等,慢慢探索各種社區營造的方式、建立羣體的故事。
在進行這些訪問的同時,我們發覺必須好好追溯「社區營造」在香港的歷史進程,這才知道未來將要走怎樣的路。其中,不可不說的,是社工曾經在早期「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簡稱CD)擔當的重要位置──香港70、80年代的社區營造,曾經是由一羣行內稱為「CD佬」,專門組織街坊、周身刀的社工們推動。
但為什麼,在2015年,當我們各類型的社區正面對多方衝擊,卻再不見太多社工參與在逼切的「社區營造」上?為什麼這個社會工作(Social Work)的傳統好像無以為繼,只能靠其他專業人士參與?
我們找來了社工老師、元老級「CD佬」莫慶聯(莫Sir),跟我們回顧歷史,再找尋前面的「社區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莫Sir於1981年在社工系畢業,一出來就做CD。「70至80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社工參與社區發展的高潮期。」莫Sir說。「最高峯時,全港有54隊政府資助的社工做NLCDP。」
NLCDP,全名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中文是「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它是一個由殖民地政府於1978年開展的「社區發展」計劃。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資助的「社區營造」計劃,會聘請社工到偏遠或低收入地區,組織街坊,為他們爭取福利、改善環境等等。「這批社工不是去搞吓興趣班、做吓託管咁簡單,他們是真的可以組織街坊做抗爭,與官員對話。」莫Sir說,「其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已有人開始做社區組織的工作。最早的機構應該是社區組織協會(SoCO),在1971年成立,不依靠政府資助。但要到1978年,政府才首次開始這類型的社會工作計劃。」
哇,40年前的港英政府是如此開明的嗎?
「唔,那是他們一個聰明的政治手段,也是機緣巧合。」莫Sir說,笑笑。
70年代末,香港仍被67暴動的陰霾籠罩着,港英政府一方面相當敏感和緊張,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檢討管治策略。此時,剛好遇着內地大饑荒湧來的移民潮,山邊的木屋區像一個個不規則的堡壘,高峯期有超過70萬人住在這些沒電沒自來水的房子,社會壓力很大。
加上一羣於戰後出生的青年人,開始對香港產生歸屬感,受西方人權運動影響,經歷保衞釣魚台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污等學生運動,亦思考自己在英國政府統治下的處境。
如此種種,交匯出一個時代的臨界點。
70 – 80年代:用社區發展面對社會矛盾
「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整體都很躁動,矛盾愈來愈尖銳。」莫Sir 說,其實跟2015的香港,也有不少共通之處。「新移民潮、學生運動(當年亦有勞工運動等),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產生壓力團體、暴亂的溫牀。他們是覺得要立刻處理。」
英國人的「處理」,是先做了一個報告,判定其中一個社會當前要面對的問題是:官民溝通不足。市民不了解政府施政方針,有資源的人無法提供意見,低下階層連自己擁有什麼福利也不曉得。面對社會精英,殖民地政府面運用「行政吸納政治」,把他們納入到各類型的諮詢會,讓他們的意見(和情緒)有渠道紓解。
那低下階層又如何?「他們聰明地運用社工,去安頓和安撫他們。」
政府開始取締木屋區,但受影響的人實在太多,即使他們已經在做十年建屋計劃,都不能把所有人安置在公屋,那就惟有把居民安置到不同的臨時房屋區(或稱安置區、臨屋區、徙置區)。把貧苦人都聚集在小區,可以出現難以控制的狀況。於是政府就辦了NLCDP,招募一批社工系畢業生走入社區,訪貧問苦。
「當時港大學生會會長麥海華,畢業出來,第一份工就是去鄰舍輔導會工作,派去鑽石山大磡邨做社區工作。那一代做社區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有學運的背景。因為社區發展工作,在社會工作裏面,是最有社會改革面向的。它提供一個機會,給曾經參與學運,希望推動激進社會改革的學生,讓他們可以找到工作養家,同時亦能實踐他們想做的理想。」
那政府不怕他們會「搞事」嗎?
「他們被分派去的,都是過渡性社區,是暫時性的,」莫Sir 說,摸摸下巴,「再加上居民當時都是低下階層,是比較實用主義的,基本上是很難politically建立成一種力量。」這批CD社工,通常是3、4人一個小隊,就處理一個10,000人的社區。「你咩都要做囉,小朋友託管、家庭調解呀、搞大旅行呀、幫手申請上公屋、組織街坊要求改善環境呀……一腳踢,但我們不介意,因為是真實地在解決人的問題。」
沒有區議員、沒有蛇齋餅糉的年代,所謂「社區工作」,就落到「社會工作者」身上。
「回看70年代的NLCDP,它其實是在填補兩個 gaps,一是service gap,當時市民對於福利、社會服務資源不太掌握,社工就可以幫他們解決,幫小朋友補習呀、搞親子活動呀。另一個是political gap,NLCDP也是一個政治措施,是一個疏導的渠道,去穩定社會。」
「我只能說,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很聰明。」莫Sir 說。
90年代:由社區發展到帶領貧苦者抗爭
但重建、拆遷,很容易會連上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社區發展,到最後還是會連繫到自由、公義、尊嚴,甚至民主等議題。這個「聰明的」殖民地政府,到了90年代,終於要面對連串抗爭。
90年代起,有一批社工眼見示威、遊行,對政府的影響漸少,開始想採取一些較激進的行動方式去表達訴求,這批人被稱為「新社會行動」。
「他們不會跟從以往的規範去做社會行動,他們主張解決社區問題,是要由大家一齊坐低平等討論;只要大家有共識,是可以不順着議程討論,例如明明講緊某個住屋問題,一下跳去講警權過大又得。如果有警察來查,要求查看負責人的身分證,他們會話我們這裏個個也是負責人。」
那不就跟上年的……「是的,他們的理念,甚至行動方式,和雨傘運動好相似。」莫Sir 說。
1993年,房委會強行推出富戶政策,不同社區組織組成「反公屋富戶政策大聯盟」,在3月25日於港督府門外的上亞厘畢道馬路上靜坐堵路,要求新任港督彭定康接信,最終27人被捕。據參與者稱,聯盟內正是實驗由下而上參與民主,行動方向、立場等,都是由所有人共同即場決策。1994年12月,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的社工與荃灣德仁樓、卓明樓天台屋居民,帶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煮食爐、石油氣罐等等「瞓馬路」,抗議當局清拆他們的住所但卻沒有作出合理安置,結果社工與居民被警方拘捕。
「合一中心是和社區組織協會差不多同時期開始的民間CD,但前者走一個比較激烈的路線。它並不是唯一走『新社會行動』的機構。事實上,當時社會行動是和社工分不開的,這是他們工作一部分。不像現在,因為社工專業化,他們的參與就愈來愈少,社會行動就交給文化研究呀、社會學的人去處理啦。」
回歸前後:社工專業化,從社區發展退場
「合一事件」以後,政府停了NLCDP。社會上曾經有很多聲音反抗,甚至行政會的成員也不支持停止社區發展。然而最後,經過改名、修訂服務內容和規定等等,搞了好幾年,NLCDP還是沒有延續下來。本身有做開的社區,可以繼續,但不會再接受任何新申請。根據社署資料,2012年,全港只剩下17隊NLCDP社工。
「他們大都在較偏遠的離島、新界。這些地方的鄉紳勢力大,根本不用政府出手就可以控制他們,很難做到組織街坊。」莫Sir說。
但政府不資助,還是可以由民間做起呀,不是嗎?「沒有資源,也就沒有機構願意投身這個範疇。社會福利署evaluate機構的指標,都是很量化很數字的,但做社區營造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基本上政府是揑住了社福機構的經濟來源,無錢真的無人敢做。」
而為了迎合政府或公營機構的標準,社工形象和訓練亦要走向「專業化」。「所謂『專業化』就是強調個人性、治療性,而且必須維持社工的社會地位,不可以做爛仔,要強調自己的專業獨特性──而抗議示威並不是我們的獨特專長,因為抗議人人都做得啦。」
「所以,並不是一個單獨因素,令社工在社區發展和社會行動上退場。90年代的抗爭事件、社工專業化,加上跟政府之間的利益糾纏,令大家也很難有發展空間。」
雨傘以後:社工運動可以復興嗎?
社工退場了,不代表社區發展不可以走下去。由利東街開始,社區發展的議題開始由各種背景的專業人士,聯同街坊共同策劃、參與。莫Sir覺得這樣絕不是壞事,反倒令社區發展的方向更闊更廣。他坦言,今天的社區發展,「唔好再旨意社工」。
「社工界的工作有3大方向:solve the problem, prevent the problem, community development。而好明顯我們現時只是在做頭兩項,青年人升唔到學喎,我們就搞更多的升學就業計劃,等他們可以盡快投入資本家的剝削裏面;又或者係濫藥喎,我們就搞個計劃去防止濫藥。」
「也不是說這些不重要,但現時社工的專業化訓練裏面,只注重教人怎樣見case,點開小組,但對於文化批判,社會脈絡的分析、政治環境的影響,是沒有太多討論。呢啲嘢,交畀社會學啦、文化研究啦。我們講社區營造,已經不是只講人在社區內的生活問題,而是落入一個更大型,抗拒單一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抗爭裏面。而現時社工本身的訓練並沒有這樣的視點。」
「社工是最叻建立關係,但最後想透過這些關係帶出一個怎樣的信息,是沒有太多的反省。」
可是,在雨傘運動期間,許多社工也積極以個人身分參與,他們本身對社會運動也有很強的投入感,不是嗎?
「當然當然,問題是回到工作崗位後,他們完全沒法滲入這些理念。如果你是以社工身分去參與一場運動,你就要發揮這個專業的獨特性,例如你會帶領街坊和長者,一齊去了解這場社會運動,陪他們去明白或者觀察;又或者是把這個議題帶回你的小組,讓公公婆婆都可以討論和了解。」
「無嘅,如果我哋返工只係同佢哋唱生日歌,放工就自己支持佔領,咁即係咩意思呢? You yourself can be very radical, but the profession itself is very conservative. 我們教學會講社工要重視人權和自由,要做到 liber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people,但真正可以在職場實踐多少?」
莫Sir強調,他對社區發展並不悲觀,他只是對社工行業繼續依賴政府資源,覺得悲觀。但與此同時,由一批社工於2013年開始的「社工復興運動」,於雨傘運動後出版網上雜誌《社福街15號》,推動社工界與社會運動更多連結,「讓社會工作者重拾智性工作的習慣,以深耕細作形式逆權抗爭」。
「我的立足點是悲觀的,但仍要有盼望。或許,當我們集結到一定的數目,我們就能推動改變。」他說。
(全文完)
text by Dy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