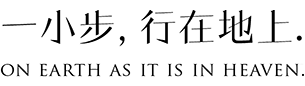聽其他農夫說,若想搶早水冬瓜,過農曆年前就得培苗。是故一月中下旬的時候便試著將上百粒冬瓜種子落地,心裡想著的就是趁我們到處吃喝打麻雀歡聚的時候,種子會自已悄悄的開口,兩片子葉趕出來與我們拜年。
結果是失敗的。
看着種子在泥土裡毫無反應,看見甚麼蛛絲螞跡也會份外竭斯底里:是不是缺水?還是溫度仍然太低?是不是覆蓋太厚?田面有部份覆蓋的乾草被揭開了,是老鼠還是餓得開始要鑽地了?甚麼理由也好,或根本就是多個因素的結合,兩三個星期過去,只好重新培一批苗。這次為了增加發芽機會,專誠找書看及求教於google大神,看有沒冬瓜的浸種催芽秘技。多少個搜尋結果就是多少個師傅,每個答案也不一樣,共通點差不多都是冰火幾重天,不同溫度的水反覆浸不同時間。結果第二批種子浸了一晚室溫水,然後再用濕布包好,每天洗水換水一兩次,三四天下來種子才開始裂口,驚蟄前後才安心把種子下地。
這次育苗的經驗,彷彿又讓我了解所謂耕種多一點。若農民能夠以陽光、水及泥土為原材料,雙手將一大冬瓜雕塑出來,人類便無需要種植;退後幾步,若人能控制種子發芽的溫度濕度條件,種植也許亦會輕鬆得多。以主客關係視之,種植其實不以人為能動者。基因工程也好,溫室等人造環境控制技術也好,無論科技多麼發達,植物本身才是雕塑師,才是整個過程的能動者。種植不同作物,只是農夫拜託不同品種的植物,為我們雕塑出不同造型及養份組合的食物。只可惜植物自身不能開貨車,不能在市場上磅及講價,人才有發揮僅餘技能的餘地。
近讀美國生物學家羅伯‧唐恩的科普作品《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裡面提到世界上有種名為「切葉蟻」的蟻類,牠們是大自然裡少數需透過栽培為生的物種。從另一角度描述之,切葉蟻這品種將其消化系統「外判」及「委托」予一種真菌,切葉蟻將切碎了的葉片運回蟻窩裡,餵飼給窩裡的真菌,真菌便將葉片分解及轉化為蟻可吸收的養份。切葉蟻及真菌不僅成為生物學上互惠共生的經典案例,一個物種作為別一種物種的體外消化系統這意象,本就引人入勝。
書裡提到的另一例子是連接盲腸的「闌尾」。闌尾切除手術是至今其中一種最常見的外科手術。直至二十世紀下半,闌尾均被視為無用的、正在退化的器官。後來才有科學家指出,闌尾其實是人體裡的一個避難所, 若腸道受病菌感染而需要「大掃除」時,人體內各種原生細菌便可躲在闌尾,避色被一同排出體外。現在發達地區的問題,不過是由於免疫、消毒等的水平太高,闌尾所屬的免疫系統才出現失調的現象。換個喻言一點的說法,以往所謂「人」的免疫系統,其實需要不同的細菌、真菌等所構成的多樣性來維持,即多樣的細菌與人的健康並不互相排斥,又或沒有一種零細菌的健康。
即使以區隔、消毒等為主流價值的西方醫學、科學,晚近的研究成果都在告知我們競爭及鬥爭不是物種間唯一的關係。驚蟄所代表的世界觀似乎又值得叫我們重新思考了。驚蟄正值春耕農忙,之所以農忙,就是以動植萬物都從冬眠醒來或泥暖發芽等跡象來說明的:沒有這些跡象根本就無從說耕種,環境仍然是人的意識行為的充份條件。遠古對自然規律的總結,原來歷經工業革命及二十世紀的科技發展,才份外顯出其超越時空的普世智慧。
–
作者:周思中,生活館成員,一星期兩天教書,其餘時間下田。
生活館:成立於石崗菜園村搬村前一年,三年前搬到錦上路謝屋村,在大約三萬呎的農地,夏天種米,秋冬天種時令蔬菜。晴耕雨讀,閒時造麵包醃泡菜。在農務之中探索香港社會發展、泥土微生物及人的關係、及如何終極擺脫現代社會的各種宰制。換言之,如何重建美好而不依賴的集體生活。https://www.facebook.com/sangwoodg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