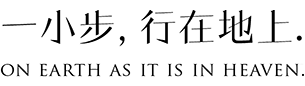錦田匯動文化館(看另文:本土到最根本,才是對世界最有意義)的下層是公共空間,上層是圖書館。今年五月,這裡有一個《記憶郵件》攝影展覽,參展的攝影師除了有本地視覺藝術系的學生,也有尼泊爾藉的青年人和來自非洲的尋求政治庇護者(Asylum seekers)。
今年一月,浸會大學「憧憬世界」攝影教育計劃與突破匯動青年合作,在錦田開始了「記憶郵件工作坊」,他們選擇了錦田作為根據地,攝影工作坊導師包括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及加州藝術學院的教師帶領學員進行一連串的訓練。第一階段先要學習攝影技巧;第二階段則要透過作品表達自己;到第三階段,學員要拍下對錦田這個社區的感受。
看見了錦田的……
錦田在都市與鄉郊之間,是香港少有融和兩種特質的社區。這裡有很多村屋,也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居住,還有傳統的圍村。因為位置偏遠,租金較便宜,不少來港尋求政治庇護的朋友都會住在這裡,不過西鐵站通車之後,租貴了不少,但他們在這裡仍有一些社群。
Kbrom來自厄立特里亞(Eritrea,1993年由埃塞俄比亞獨立出來的國家,至今政治經濟狀況仍未穩定,邊境仍有與埃國的零星戰役),現在住在梅窩,他被錦田的圍村深深吸引着,他的攝影作品就是一座圍村內的廟宇:「我覺得它很有趣味。」異鄉人的眼光令Kbrom揭示了錦田的最獨特之處。
回想從參與計劃到作品展出的過程,Kbrom說這讓他慢慢地學習享受成為一個攝影師。居住在離島的他,本來所踏足的社區並不多,學習攝影之後,他的好奇心亦逐漸被開發。「除了錦田之外,九龍城也是一個很吸引我的社區。」。
「這裡很像我的家。」同樣來自厄立特里亞的Moki拍攝其中一個展品時,看見一幢正在興建的建築物,卻意外聯想到家鄉,結果便將之拍下,最後更於成為展品。他續道,「錦田給我的感覺,很像我的故鄉,有鄉郊、有興建中的大樓,跟其餘的香港很不同。這幢興建中的大廈,令我聯想到家鄉許多建設,所以就把它拍下來了。」在外三年多,愁思其實在一物、一念之間就可以觸發,若果可以用藝術方式表達,更可以成為他人的祝福。皆因每個人,心中都有多愁善感那一塊。
另一受訪者Darius來自多哥(Togo),其作品是一幀藍天,加上許多電線桿。「這是我看過最美的藍天!配上電線桿,很像我家的境象。」陽光依舊燦爛,藍天依舊浩瀚,只是人已不能在家鄉奮鬥。Darius在大學時主修法律,除自己的非洲母語,還會說英、法、德語,加少少廣東話。「我很高興自己可以重獲新生,但同時我還是很想念我的家鄉。不管如何,我都會記得我從哪裡來。」從Darius眼中的堅定,便會發覺,在絕望的處境當中,沒有什麼比心存盼望來得重要。

上圖是Darius的作品,下圖則是Moki的作品
看不過眼的差異?
來到香港,他們都受到一些文化衝擊。Kbrom說,「香港人很多時都是出外吃晚餐;但在非洲則相反,九成時間都是回家吃飯的。可能一年只有兩三次會在外邊吃飯。」Darius立即點頭稱是,「香港人都比較集中於自我,每天在街上,都看見他們只是看着手提電話,不願與別人面對面溝通,與親人吃飯的時候也是如此,但其實食飯是最好的溝通啊。」
「還有我完全不明白,為何吃飯時女生要付錢?」Kbrom繼續說,「香港人吃飯到最後會各自夾錢,我最初都覺得很怪。在我們的家鄉,出去吃飯女生是不可以付錢的。另一邊廂,男生也不可以煮飯。我們的性別角色是明顯分別的。」然而,在港的生活令他們都突破了自己的「comfort zone」「現在我們都會煮菜了!Moki煮的食物很好吃。」
看不見的未來?
在港的尋求政治庇護者每月只能有一千五百元生活費,也不能找工作。「香港什麼都好,既專業又國際化,但缺錢的生活,還是還我們很苦惱。」Moki抵港初期,居住在交通樞紐的紅磡區,後來承受不了昂貴的租金,搬遷至租金較便宜的梅窩。「梅窩夠靜,我喜歡!雖然有點遠,譬如今早要來到錦田,大概六時就要準備出門了。」他正在申請前往美國或加拿大,「但似乎確認申請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我想也只好繼續留在香港等。」可是,這一等,可能兩、三年,也有可能是二、三十年。
那麼,在漫長的等待中,想得到任何堅持下去的理由嗎?Kbrom說,「儘管不能工作,但至少在這裡,我體會什麼是自由,什麼是良好的治安。」也許自由實在太寶貴,寶貴得生活上的其他困難也可以忍受,至少在他們的家鄉,自由並不存在。「在香港,我找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會感受到壓力。」
也許香港一直只會在他們心中的中轉站,但願他們在這裏能看見「希望」的中轉站。
text/ Haha
edit/ Lokman and Dydy
photos/ Andy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