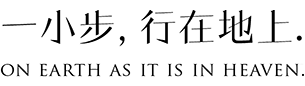要講南涌和活耕建養地協會,就必須要細緻地描述我們所見的一樹一木。因為整個旅程,除了是看本土生產,幾乎是一個靈性之旅,盡收天地靈氣。
這也是南涌最扣人心弦的地方。
那天我們跟「港嘢」夥伴約好在粉嶺火車站集合,一行10人,剛好趕上了10時正的小巴。
「呵。半小時後才有下一班車呀。」寶熙說。她、May和蒲公英都是「活養建養地協會」的執委,協會推廣南涌的鄉村生活文化、復耕和自然建築,當然最主要的,是「夾錢養地」。到底是一塊怎樣的地,讓他們和其他會員,願意花錢去「養」?我們心裏想。
大半個小時的車程之後,才在海邊的天后宮路口下車,寶熙和May帶着我們,沿着直路走了5分鐘,就會看見香港如今難得一見的風景──魚塘、候鳥、蘆葦、紅樹林……縱然大夥兒仍在交談,環境就是有一種不能形容的寧靜。
「這種鄉郊直路是分隔線,一邊是V area(鄉村用地),另一邊是AGR(農業用地),即不能起屋。」May指指楊屋村的路牌,「以前我們帶導賞團的話,通常會由這裏開始說啦,呵。」南涌有幾個姓氏小村落:楊屋村、羅屋村和鄭屋村,都是客家人。
南涌的地理環境適合耕種,魚塘下面以前都是農地,但隨着很多村民出去城市生活,這些魚塘、農地都荒廢了。這片紅樹林是供候鳥冬天棲息的好地方,冬天紅樹林枯了,凋零,有另一種美。
「唉,上次嘉道理的人來看過(紅樹林),是生病了啦。你看,這邊的水位愈來愈高了。」May說。
另一邊的魚塘,長滿了蘆葦,隨風擺動。
若不是因為在採訪,這個風景,真的可以看一個下午啊。
「這裏本來種了蓮,之前土作坊月餅的蓮蓉,就是用這裏的蓮子造的。這一兩年因為這些蘆葦,產量少了很多,蘆葦也不是沒有用的。可以用來編織,只是我們沒有人力技術而已。我們也有蘆葦筆工作坊呀,只是真的太多了,寫不了那麼多呀。」寶熙苦笑。「若資源許可,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動工程,抽掉塘裏的水和做高一點去水位。希望可以重新再種蓮子啦。」
行近農田,農夫何叔叔的狗兒們全都跑過來向着我們擺尾,嗅嗅我們,好像知道我們是主人的朋友,都沒有吠。超乖的。
地是怎樣養的?
「無人會好像我們這樣,租『地』租到9成是魚塘,只有1成是地。」May和寶熙笑笑自嘲。早年南涌的居民把農地灌水做魚塘,因為當年養魚的利錢較高,後來不少居民移民外地,魚塘就丟空。協會租了魚塘回來,裏面的魚是用來「請」候鳥吃的。而協會「養地」,則是為了與大自然共生,保育南涌這個地方。
2009年的菜園村事件,喚醒了很多香港人的「土地」意識──有人醒覺土地是生命之源,投身土地正義的運動;也有人發現原來香港的地是被「發展者」看中之後,才變成生金蛋的鵝……
南涌鄰近沙頭角,幾年前沙頭角的發展界線未明,有人偷偷在南涌傾倒泥頭。寶熙、May,和「永續農業協會」的其他朋友心慌了,快手一起夾錢租了面積約110斗(1斗大概是7,500呎)的魚塘和耕地。他們在這裏搞永續農耕、生態導賞、社區廚房等活動,希望多些人認識也一起保護這個地方。3年之後,租約期滿,他們成立「活耕建養地協會」,招收會員,期望用一個「更持續」的方法,保育南涌。
現時協會有50多名會員,每年交年費(HK$2,400),夾錢「養地」。「會員的義務嘛……就是出席會員大會囉,也不容易啊,香港人真是很忙呀……」May苦笑。寶熙覺得,這是搞運動必經的階段,「是認識會員的過程呀,我們初頭會期望會員們出錢,出力,出時間,最好大家認購這裏全部農作物添啦。後來發現這樣想是不切實際的,可能有些人有錢支持,但未必有時間……能付出勞力的,又未必想交會費,蘿蔔一出就幾百斤,會員又未必是家裏負責買菜的那一位……」
遲來的執委蒲公英補充,「加上現在社會出面處處都是火頭,每個人在生命不同階段想做其他事情,完全無問題的。」
「所以我們現在會較開放地想,」May總結,「會員大會會開放給非會員參與,讓多些人知道我們的理念,非會員也可以給意見。對外導賞每次都會講協會的運作和理念,招收多些新會員。」
推動一個「養地」運動,幾年來,行政的工作,教育和宣傳的活動,肯定耗掉很多心力。現時協會有6個活躍的執委,負責籌款,找新會員,教育和宣傳,搞活動……對於招募新人,「這個要看他個人和這個地方的緣份了。」寶熙強調,「這個是最重要的,好像我自己,是先被這個地方懾住,這是個人和這裏的connection。」是的,只要到過這裏看看,就會有動力讓人想去保護這個地方。
營造「中小農」的環境,可以嗎?
在南涌復耕的本來只有何叔叔和輝哥,去年開始就多了4個小農,在周邊租地,擴大了復耕的範圍。May 這年開始也是其中一個小農,「因為耕田,跟村民熟了好多,(會談什麼呢?)會談什麼嘛……」她尷尬,「就是常常問在種什麼?因為搞來搞去都未種到什麼出來啊……哈哈。」
好好在南涌復耕,是他們的目標。談到近來政府做的農業政策諮詢,May和寶熙都嘆氣,「好明顯就只是想安置東北發展後的農民吧。」May 提議,若政府收荒地稅,地主就有動機租給人耕種,這比起另闢土地搞農業園實際好多,反正荒地很多,有人都想耕田的話,就可以在荒地復耕。「你要耕田,有了地,也要做工程,最少要做個圍欄,攞電,搭條水管,5至10萬元走唔甩。」漁農署會有資金給一些已開始的農場,但個體戶農夫是沒有資格申請的。
「唔通去銀行借咩?」做生意去銀行借錢好像很合理,阿里巴巴馬雲都注資給年輕人創業啦。做農夫?……「做農業不同做生意,回報是慢好多的。」May指出,若政府有心認真搞農業,可以給種子基金農夫,每人10萬,讓200人在港復耕,才2千萬。「現在要收回70公頃搞農業園,又不知道搞幾多個億出來。今時今日,有本土、安全的食物,香港人不知幾welcome,連荔枝窩都有人專登入去耕田呀!怎會沒需求呢。」
寶熙補充,「做有機、永續農業,是不能單打獨鬥,因為是在說整個生態。農業園沒有社羣的關係,也沒有整體保育生態的想法,人人打蟲(藥)你不打,點搞有機?你死梗啦!」
長遠來說,他們希望南涌發展成「生態村」,農地有人復耕,有自然建築,鄉村裏有人生活,「希望不用常常往返城市的人,好像從事文字、藝術的自由工作者入來生活。」若由在南涌真實生活的人去話事,去組織,慢慢這個在地的社羣可以自發搞多些新事。
唯獨南涌
聯合國教科文組識提出,「生態村」(eco-village)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除了環境、經濟、社會,還有人的靈性。「這是南涌很適合做生態村的原因,你來過,你就會感覺到這裏的靈氣……為何要講靈性?人心不轉變的話,還搞什麼持續?」May說,「以前在綠色NGO做,常常講可持續,自己忙到死的,其實這就最不可持續。」眾大笑,這正是今日香港人的死穴:割裂。
每個農場在香港僅餘的農業裏,都有自己獨特的角色,「南涌嘛,是一個很寧靜的地方。首先你不能只來半小時(搭小巴都半個鐘),最少半天啦。」令人最少花半天時間一起的南涌,環境、生態都觸動了很多城市人,「她」的靈氣,很適合成為生態村,May說,「所以我們真的好想keep住這個地方」,而不是發展,或荒廢。
「我們要重新尋找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是不斷榨取剝奪,還是被滋養?人心,是不能被物質滿足的。在南涌,會找到一份心靈的滿足。」寶熙說,「我們常說在養地,但其實這個地方給予了我們很多很多……與其說是人養地,其實是地養人才對。」
text/lokman
photos/ andy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