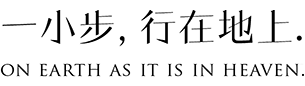姍:
謝謝你。如果說學到什麼、明白了什麼才可以寫給我的話,我想,你每一張postcard都可以給我一個copy。每次收到你的信,都是感動的;即使是上次你遞來的辭職信,我看的時候也幾乎哭了出來。
你每星期的Working Holiday週記,我是每篇都細讀。上次你寫到工廠就像小型聯合國,從各人離開本國的時間,看見歐洲當年的動盪如何觸發移民潮,再回想今天的香港,這種見微知著、以小見大,也不是一般寫作人能做到啦。
近來看你寫工廠的粗活,一下子把我帶回上世紀80年代末。那年的暑假,我幫親戚打工,做跟車,賺錢買機票去台灣旅行。我家以前是做油桶的,就是那些在電油廠一桶桶、豎直起來大約半個人那麼高、容量有200公升那種油桶。這生意本是我阿爺的,做法是從各處收集清空的油桶,再轉售給其他行業,例如,地盤的臨時垃圾糟就是打通桶底桶面再焊接而成。到親戚接手時,這行業的環境已大不如前。當時我的工資是HK$70一天,去台灣的旅費是HK$2,100,加上平時節衣縮食,總算目標完成。
事後回想,那段日子留給我最寶貴的,不是區區金錢,而是流血流汗的勞動生活。雖然我讀幼稚園時,已常常隨家人送貨,坐上那紅色車頭、綠色帆布的噸半貨車周圍去,但真要付出勞力,這是頭一趟。
很記得,那時每天把100個各重40餘磅的鐵桶,搬來搬去,從貨車車斗上貨落貨,在泥地和後巷一個個的疊高,如何使當時只得110磅的我操練成鋼條,指力和臂力大增,去到一個地步,寫不出字來──因為筆桿太輕,寫字時手指用力太細緻,控制不了筆畫。然後我明白,為什麼要勞動階層寫字是那麼的艱難,字形為什麼總是歪歪斜斜,紙背何以隨筆尖深陷。
這也不算最深刻。因為這工作,我每天總是穢穢的,背心、短褲、拖鞋是標準套裝,惹來巡邏的警員常常在街邊查我身分證。雖然我也沒犯什麼法,但那種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被問長問短的感覺,也許查問的警員沒什麼感覺,但被查的人原來會不期然的產生自卑。更自卑的感覺,來自十來歲的男生,蹲在工廠區的街邊捧著飯盒食飯,眼前身邊飄過的,是放午飯的工廠OL。那時,我連頭也不敢抬起,緊繃著身體,怕弄髒這些青春少艾的裙擺。
每天放工,疲累的身體使我一上巴士就睡。好幾次都睡過了頭,本來在屯門下車的,差不多到了洪水橋才忽然驚醒。有時,太陽猛烈,身體吸了一天的熱,晚上睡覺時,熱氣隨著皮膚毛孔散放出來,整個人都被一層無形的熱氣包裹著,風扇的風吹過,就像撥過熱燙的溫泉,風一縮回,熱氣就重新包圍。那時一個人,最愛流連的是商場裏租借錄影帶的影視店,坐在櫥窗外的梯級看娛樂片,腦袋放空,什麼也不想。
勞動工作,事實上一點也不浪漫。對讀書人來說,由身體到心靈以至身分上的衝擊,是那麼實在,當時那刻說什麼勞動光榮,說是屁話也不為過。
然而,這也是我人生中一段一再回味的日子。不是有什麼可誇,而是,這段經歷使我一生不忘,這個世上,有些人是活在如此的人生視野中。當我說什麼高闊偉大的事,這段日子就要我回到根本──What does it all mean to this kind of life and people? 我不是要為其他人尋找意義,我只是要問,這些說法對當時的我是怎麼一回事。這也不是什麼抽象的意義思考,而只是,當時的我如果聽到有人這樣說時,會聽出什麼來。
知道你近來心情不好,天未光就趕上班、一下班就趕上課,加上陰冷的天氣、太早下山的太陽,一聽見就想到那份壓迫感。姍,慢。慢。來。不趕的。真的不趕。太急迫的話,就本末倒置了。
這幾天,我捎來那閒置了很久的愛爾蘭小笛子,在找些曲子練習,碰到了這首,是《魔戒》中甘道夫前往哈比人村落時的配樂。那些勞動的樣子,讓我想起,為什麼說牧羊少年都愛吹笛子。這些小巧的樂器,真會把人帶到另一個節奏、另一個世界。這首歌,這個畫面,送給你和猴子。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 Howard Shore – Concerning Hobbits (The Shire)
Pak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