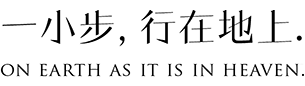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編按】 我們香港人,最關心的是「住」。有人形容當今是共居年代(The Year of Co-living),共居公寓應運而生,似為年輕人解決居住出路,亦是商機;政府更於年中注資興建青年公寓。另一邊廂,民間團體自發為急切住屋需要的基層人士,以低於市值租金的共居方式,提供住處。亦有人倡議要帶着共同理想入住一屋。
但是,什麼是真正的共居?共居要解決的只有住屋問題嗎?把房間劏開分租也是共居嗎?共居原來的精神是什麼?共居的生活環境又應該怎樣?我們可以從外國的共居例子借鑑嗎?香港人透過共居,除了有所棲身,其實更可以創造什麼?
問題太多了!2017年終、2018年初,一小步有一個小小的共居專題,繼上一篇藍屋共住社區參觀記,再請來對歐洲佔屋運動頗有認識、用行動開拓在香港生活可能性的龐一鳴,跟他一起梳理共居的由來,以及了解當人云亦云共居時,我們如何正本清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前,人都是共居的。
一個十多人的大家庭,或者幾個家庭共住一間房子是常態。
直至資本主義誕生並告訴我們:私人空間是至高價值,擁有不受其他人干擾的空間和時間才是美滿人生。
於是我們離開一大羣的親人,組成小家庭,兩個人、一個人住一間屋。這樣的模式,除了令房子好賣,還讓電器的銷售節節上升,能源使用突破新高 —— 資本家當然感到好滿意。
利潤經過多年攀升,終來到了平原--因為許多人都無法追趕到那尤如天高的房子價格;為了生出新一輪利潤,資本主義最近又說話,說:住在一起是好的。
於是我們又住在一起。只是這一次不是和家人共住,而是和一班陌生人。
每晚爬進專屬的太空倉,共用客廳的豆豆沙發、共享配置了微波爐的廚房,還只能躲進廁格才可以用hand-free接電話。
當然資本主義這時候會說,在冷漠的城市中有個照應才是至緊要的溫暖人情味呀,我們還可以交到很多有趣的人呢,這樣生活才有返血色,似返個人,諸如此類。
於是我們又不介意付出比豪宅更高的呎價去和一羣不認識的人共住。無論共居,或是不共居,資本主義的教誨都成為我們做決定的依據。
可以讓「共居」不被騎刧嗎?
回顧2017年的香港社會,「共居(或共住,Co-living)」一定是其中一個關鍵詞。
過去兩、三個月,更是媒體討論「共居」的高峰期:有以居住層面探討,有以潮流文化的面向作報道,但最多篇幅是來自各報刊的財經版,以商機角度分析當中的投資回報。
談及所謂「共居」的計劃,定議和內容更是五花八門:一方面有政府與社聯合作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針對基層的住屋需要;又有政府和NGO合作的青年宿舍計劃,嘗試協助青年有房住又可以儲錢;亦有聖雅各福群會在藍屋推出「好鄰居計劃」,嘗試在活化建築和社區營造上找可能性;還有幾位年青建築師、圖則師開了一個名叫「共居香港」的專頁,招募潛在租戶、業主、共同生活的夥伴,更開Event「共居FF」招聚人一齊傾下如何開展民間共居計劃……等等。最後,有利可圖的地方當然都會有商人的蹤影。有公司早於兩年前已開始整幢唐樓買回來,裝修後以共居名義出租給青年人,短時間內已發展到在各區發展了10個類似唐樓翻新成「共居」計劃。
但,到底什麼是「共居」?我們純粹是要住在一起嗎?如果,把空間平均就是「共居」,那豈不只是「劏房」嗎?(建議大家參閱2017年11月5日《明報》的《未來城市﹕共住,根本就是劏房》;當中談及共住的本意,外國共住的歷史傳統,由女性主義者以此打破「男主外、女主外」的規範,到建築師透過共住鼓勵社區參與。)
當社會看到有必要以「共居」來對應房屋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需要認真看看「共居」在過去幾十年來,於世界各地的實踐。這才能避免「共居」成為另一個來到香港後,水土不服或是被人騎刧的概念。

荷蘭境內最大的佔屋,是此前天主教醫院,現已開放作文藝用途。(圖片來源:維基)
佔屋也是共居的一種形態!
如果「共居」的定義,是指陌生人共住一個空間,互相照應。那麼在西方,大規模的「共居」早於二次大戰結束已經出現,而且是以非法佔屋的形式出現。
以英國為例,由於二戰期間停止建屋,加上打仗期間,德軍空襲完全摧毀了近20萬房屋,同時令近25萬房屋無法再住人,1945年戰後的英國,失去了近70萬可住的房屋。結果英國出現大規模的佔屋運動,低下階層為有幾塊瓦片遮頭,只好和很多人擠在幾近頹垣敗瓦的廢屋中。
這當然毫不浪漫,也絕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很光亮美好的「共住」印象。
但由此而來的「佔屋運動」,就在歐洲各國持續出現,並延伸成為一種獨特的「共住」模式和傳統,作為抵抗住屋商品化、「居住權不再是人權」等等社會不公的情況。在民眾運動生命力較強的國家如荷蘭、德國、西班牙等,在過去30年都出現持久和大型的佔屋運動,其中又以80年代初為高峰。
荷蘭一直是「佔屋運動」中名列前茅的國家,當地民眾對於「居住權比房子擁有權」重要,有普遍的共識。雖然,它在2010年已就佔屋刑事法立法,但佔屋的傳統仍然以各種方式延續,甚至影響了政府的房屋政策。
2012年,我有幸在短暫入住兩個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佔屋單位,勉強有丁點親身經驗可以分享,希望可以引發大家對於共住與居住正義之間的討論。
來自英國的Simon,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一座有花園的大宅。沒有人知道這大宅為何荒廢,但Simon 已在那裏住了2年。他恪守佔屋運動一直的傳統 ── 任何人佔領了空屋,都要開放空間讓其他有需要的人入住。當年,我和其餘3位來自香港的街頭藝人一同入住,大宅裏已住了9人,最近入伙的是一對來自匈牙利的情侶。
Simon 來了荷蘭13年,一直也是用佔屋為家。我們用當天賣藝賺來的20歐買餸,親自下廚答謝他和其他共住伙伴的招待。在晚飯交談中,才知道這也是佔屋運動的另一特色:各住客都會按自己的能力為共住的單住作出貢獻。
懂電工的就幫手重新接駁水電,懂木工金工的就製作家具,有人會搬來簡單的裝置,搞定免費WiFi,也有人會主動做花園修葺等等。在社區裏面,一間本來空置、雜草叢生的空置廢屋,因為一幫各展所長的人,而漸漸變成有生氣、頗舒適的住宅。
如果我們一聽到「佔屋」,就立刻把它定義為「廢青」破壞社會秩序、強佔他人財產的無賴行為,就無法理解佔屋運動的正面意義。它可以讓一個本來失去價值的空間復活過來,得到善用,甚至同時讓一個社區重新有活力;也讓許多追求不同生活模式、處於各種人生階段的人們可以共展所長。

Simon在阿姆斯特丹所佔來的家,開放為共居住宅,作者龐一鳴便曾經入住。(圖:龐一鳴)
合法佔領政府的空置大會堂?!
離開了Simon的家,我有幸入住另一個佔屋單位,而這一次更令我這隻井底之蛙尖叫 ── 原來,有一些「佔屋運動計劃」竟然是由政府委託NGO幫忙協調營運!
透過Couchsurfing網絡,我認識了Franky,他讓我入住他那如同小禮堂一樣大的房間。他的「房子」,其實是阿姆斯特丹市內一座空置了的大會堂,近年因為興建了新的大會堂就空置起來。目前,裏面住了十多位「佔屋者」,他們每月只需要向負責管理的NGO,付出象徵式的房租就能安居於此。Franky在麵包工場上班,每天凌晨三時就會踩45分鐘單車返工。我和幾個香港來的街頭藝人,黃昏賣藝回來後總會看到正在休息的Franky從工場帶回來給我們的麵包,我們亦會把握他上班之前的時間,與他一起喝喝啤酒、傾傾偈。
為什麼政府會開放官方建築,讓佔屋者光明正大地入住?這還是要追溯到荷蘭一直以來的佔屋運動,讓民眾普遍認為空置的官方建築比私人空置住宅更應該開放讓人佔用。於是政府只好想出方法回應:制定政策,由官方間接營運的佔屋。
政府選擇部分空置建築,委託NGO協助管理,開放給佔屋者入住。Franky 等佔屋者要跟NGO簽合約,承諾若政府有需要收回建築時,佔領者必須跟隨安排遷出,不可以「賴死唔走」。這可說是政府回應民情,同時又想保障自己的權宜安排。
好吧,說到這裏,大概大家都會問:為什麼討論香港共居的潮流時一定要引入佔屋運動的視角?

佔屋和共住作為住屋正義的思考
2017年8月,市建局高調捐出14個位於旺角的安置單位做良心劏房,政府藉此表示自己很關注低下階層的住屋狀況。
媒體即時引述民間團體2015年的數據,指政府還有三幢類似的安置大廈,合共有百多個空置單位;另外,2013年審計處揭發政府產業署持有174個空置高級公務員宿舍單位,當中69個更已空置15年以上;再加上兩個提供中轉房屋的葵涌石籬邨和屯門寶田邨,截至今年3月共有5470個空置單位!
捐出14個單位,相對於5470個空置單位,那甚至不能用杯水車薪來形容。
如果香港對於佔屋運動有充足的討論和認識,市民又怎可能接受政府擁有數千個空置單位,而只讓市建局象徵式捐出14個單位來回應市民對住屋的訴求?就算不立即發起有充足理據和合法性的佔領政府屋運動,市民也必定會群情洶湧地向當局施壓,要求實行類似荷蘭由官方委派非政府組織推行的有規管式的佔屋計劃吧。
可惜佔屋運動的經驗和知識從來未曾在香港廣泛討論和傳播,不單沒有形成足夠力量去開展本地佔屋運動,我甚至懷疑99%的香港人會站在當權者那邊反對合法的佔屋運動。沒有像歐洲的一樣的佔屋運動洗禮,我們只好繼續眼巴巴看著每天晚上有很多空置單位空盪盪無人住。
無疑佔屋運動是相對激進,和必需負上代價。在荷蘭及其他歐洲國家,因為有佔屋運動跑在前頭,拉闊了住屋正義運動的光譜,政府才也只好跟着營運受到規範的佔屋計劃。由於佔屋運動在香港不見蹤影,我們跑在最前的就只有呼籲善長做好人減收租的共享房屋計劃,結果官方也只需要由市建局捐出數量微不足道的單位就已經交到功課。這就是為什麼筆者認為香港必須認識佔屋,擴闊對共住想像的原因。
只要我們有更先鋒的想像和討論,政府就必須回應更多才能平息民憤。
除了佔屋運動,共住還有很多可能性;再不擴充對共住的想像,社會不只不能進步,更會送青年人到資本家的口,讓手握資本的人再賺一筆。
下回就分享我最近去參觀,令人很失望的所謂「青年共居空間」,以及其他國家如何讓共居變得更具社會意義。
Text by 龐一鳴
Edit by Dydy
| 龐一鳴將在1月19日晚上Error Friday「住在香港,是不是我人生的Error」活動中,請來灣仔「藍屋好鄰居計劃」的首批租客Juliana(也就是《藍屋探訪記:一隻貓,一羣新舊居民,串連起一個社區》的主人翁),和連結基層住客和良心業主的好宅負責人Jay 和 Summer作分享嘉賓。歡迎大家跟幾位已經實踐共住的朋友,一同創造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詳情請看這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題【可不可以住在一起?】
1. 睇真啲:藍屋共住是怎樣?
2. 諗一諗:我試過不用花錢就共住共居!
3. 看一看:共居的社會意義是?
4. 向前踏:去做一個為別人締造共居生活的媒人?
5. 做多點:我可為共住街坊貢獻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