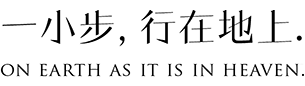編按:蘇恩佩於1972年,寫下這篇文章。為什麼在41年後的今天,要重看這篇文章?1972年時的蘇恩佩,被癌症折騰得定睛定神都不容易。本來打算從新加坡回港養病的她,當時可能沒想到,「突破」竟由一本雜誌發展成今天有200多員工、製作出不同媒體和活動的青少年機構。
70年代,25歲以下的青年人佔全港人口的一半。她看見當時的色情刊物和電影橫行,青年人也愈來愈重視物質和消費。她心裡問了一個問題──或者說,她以一個問題的方式,把自己的心向上帝敞開了──這個問題,就是「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就是這個帶病女子的一小步。
對,不用想得那麼偉大,踏出這一小步,就是「突破」的起始點。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Shalom, Shalom.”
在一群弟兄們嘹亮雄壯的祝福聲中,我帶著閃淚的微笑進入了departure gate,從此離開了我的「第五個家鄉」──新加坡。在候機室裏,上到飛機上,從裏面裂開了的心靈一直湧流出那麼多的液體,我的眼睛擦了又濕、擦了又濕。淚眼模糊中,那一張張誠摯的臉孔浮現起來﹗顯得那麼清晰、那麼真實。在那一刹我知道自己的淚水是甜的,我的整個靈魂在極其痛苦與幸福中融化。……樂意付出了全部的愛,又擁有與嚐透太多的愛,竟在人世間得以體會神的昇華。(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啊,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太值得的。於是我發誓要愛神多,要為祂的國度滴盡心裏每一滴血。
回到了我的「第一家鄉」──香港。
快有十年了,自從我離開了這地方,每次回來都是怱怱的;除了前年住醫院那次,沒有駐足超過三個多月的。這個城市發展得這麼快,已經變得很陌生了。只有天空沒有變–今年的初冬,天空仍是一樣的高、一樣的青、一樣的藍,白雲仍是飄得那樣遠。只有最高的大霧山沒有變──在這晴朗的日子,我依然可以看得見它頂上圖形的雷達站。除此以外,海洋也變了(多少個海灣已被填為陸地,我們偉大的工程師甚至在海底放進了巨型的隧道):山色也變了(多少個綠過的山已變成禿禿的,太平山腰快被一幢幢高聳的大廈斬斷了,而最近生意眼光的企業家,還在山頂建了一個形狀醜陋的圓塔餐廳);而變得最利害的乃是我們的青年人!
在陽光的日子,我常常到天台去踱步,從一座座大廈的隙間還可以窥到「小山」的一角。我的心為渴想上「小山」去,渴想得發痛(我家後面的小山印滿了我從兒童到青年時代的足跡)。小山該是多寂寞啊﹗可是快要被窒息的香港人都不敢到山林去吸取一點空氣(前一個月有母子俩清晨到一水塘附近散步,便無辜的被匪徒殺害了)﹗今日在香港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我們把自己緊緊地關在大鐵門裏,有人按門鈴,我們心驚膽跳的從大門的電眼去窺視一下誰在外面。我們不信任跟我們同是「人」的人。我們踏進自動電梯的時候,隨時擔心有人進來把我們的脖子「箍」起來,把我們身上的東西全部拿掉(恐怖的「箍頸黨」使我們的生活抺上陰影)。無論白天晚上我們若走在稍為僻靜的地方,便要提防冷風襲來,涼涼的刀鞘貼近體膚;身上帶的錢若「不令人滿意」,刀子是無情的,拿刀的人更是無情的。劫案的頻率快需要動用電腦來計算了,連「新區」家無長物的家庭也給光顧,而色情案、吸毒、聚賭、糾黨行兇的案件更是層出不窮。暴力的濫用、人命的低賤、人性的歪曲已達到頂點了。
而令我們驚心怵目的是大多數的罪犯的年齡都在二十一歲以下,這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
而政府當局喊著要撲滅罪行之際,電影廣告的色情架步仍以「世界一流」的姿態出現,而「小色狠」這類電影又仍獲准上演,還要畫龍點睛的在廣告上加上一句「兒童不宜觀看」。
而我們的教會繼續每週例常的聚會,我們的會眾都是循規蹈矩的中產階級。
(目前唯一令我興奮的是那一小撮基督徒在九龍城寨──無政府地帶──所展的工作。他們所有的是聖靈給他們的愛心、勇氣和能力,若是可能,我希望有一天把那個「禁城」裏面發生的動人心魄的故事寫出來。)
在有陽光的日子我仍然在天台上踱步,視野所及,是神創造的海水天空、近山遠山;然而當我想到這個大城市每分每秒發生的血腥的罪,我的心就痙攣。
「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我有的只是病弱的身軀和一枝禿筆。不,我有的更多──只要我真的相信「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不是嚴峻的法令,不是二十丈高的監獄的圍牆,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把我們的年輕人從罪惡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
蘇恩佩,70年代「突破運動」(基督徒文化更新運動)發起人之一,創辦《突破雜誌》。年輕時已罹患甲狀腺癌,之後一直與病魔糾纏,同時委身文化使命,以自己的生命回應社會,回應信仰,於1982離世。著有《死亡,別狂傲》、《蘇恩佩文集》一、二集。
延伸:
蘇恩佩紀念網址 http://soyanpui.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