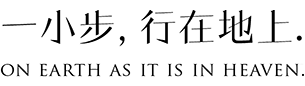寫作背景
那是1970年秋,我給診斷是癌症復發,而且蔓延到肺部。自此真相大白,我第一次對自己的病歷和病情清楚地、全盤地掌握到。到了年底,我從極度虛弱中漸漸復原,雖然鈣的平衡仍然未能完全穩定下來,但「大崩潰」事件總算告一段落。
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癌的復發不過是偶然的發現,與「大崩潰」完全無關。「大崩潰」不是因為癌的侵蝕;相反地,是因為多年前要治好癌而導致的惡果。
這是現代科技的驕傲,抑現代科技的悲哀 !?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從死亡中給救回來,不過要時刻面對更可怕的威脅。
我從來沒有身受過「癌」加給我的痛楚,然而我卻飽嚐「醫治」的辛酸。這些辛酸與年日俱增,而鮮為人所了解。當人人都是談「癌」色變,我卻聞「鈣」心寒。放射治療治死了癌細胞,同時也破壞了我體內許多正常的、健康的細胞。
我如何申訴一個一生靠藥物維持生命的病人的悲哀?
在「大崩潰」期間,我首先寫了〈只有祝福〉一文;在獲得癌症復發消息後,我接 寫了〈仍是祝福〉。是冰心的一句話引發了我的靈感,她寫道:「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冰心在她的年代,以一個年僅雙十、未經世故的少女來講這句話是不難的;我在「大崩潰」期間,身體心靈都受到極度磨折,寫出「只有祝福」這句話,自問不是隨便浪漫一番。我說這句話,我知道我的憑藉是甚麼。古代一位希伯來詩人,在歷盡人生百態之餘,寫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使徒保羅是生活的老戰士,他套用了詩人的話,並且昂然加強了語調說:「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當時我以微弱的聲音,跟 他們呼喊:「我也信,所以也說話。」
然而不管怎麼樣,在「大崩潰」期間也總有些浪漫的成分。一則當時被太多的愛所沈溺、太濃的溫馨所包圍─數不清的花朵、慰問卡、小詩、小紙條─以致在一種高潮之中,苦難也都給昇華成為祝福。
死是不難的,活下去才不容易。經過了十年後的今天,經過了更多辛酸、面對更多困難的今天,我要再寫出這句話,需要的是遠超過我自己有的信心。
今天,我仍然願意憑 信心數算我的祝福;然而今天我也願意作一點點的修正。我的生命不但有祝福,也是在咒詛底下。然而這種罪惡不算是我個人的,而是全人類的枷鎖。全人類都在罪惡的咒詛之下呻吟喘息。罪的惡果無論在人類生理、心理、及生活各方面表露無遺,它的權勢張牙舞爪地伸展到每一個角落,而我只不過是在這苦難的烘爐中與億億萬萬的人共同呻吟喘息罷了。
噫,苦難的根源不是我們此生此世所能解決的。我所憑藉的唯有是超越苦難、得勝苦難的信心。
—
「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冰心
臥病小樓已兩月餘,不見起色,小樓主人夫婦急了,和我商量要看專家。
「要看專家,就該看內分泌專家。」我這才想起哥哥以前提過的事。
遍訪之下,終於打聽到由台北最有名的專家聯合駐診的一個診所內有位內分泌專家(這類專家委實不多)。
於是展開了這場病的第二回合。
***
專家問了我簡單的問題之後,冷靜地開門見山說:
「妳知道妳是一個癌症病人嗎?」
我愕然,一時不知如何回應。
「妳多年前動手術就是為了要割除一個惡性的瘤。」
「您怎麼知道?」我囁嚅 問。
「妳家 寫信來告訴張先生夫婦的。」專家繼續平靜地 述。
原來在香港的家人見我老是康復不起來,又不知道我真實的情況,很自然地懷疑是癌症復發,一急之下決定要把真相告訴張伯伯、伯母。
我聽了倒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受,可能當時身體太虛弱,反應比較遲鈍。
接 專家聽了我的病歷,特別是那幾個月發生的情況。
「照我看,妳的副甲狀腺也割掉了,所以他們要妳服鈣片和維他命來補足。妳大概知道副甲狀腺對血 的鈣是有控制作用的吧,而鈣的平衡對身體影響又是很大的。看來很可能是妳的血鈣失去平衡。不過要先作檢驗,才能確定。」
他頓了一頓,又加上一句。
「像妳這種病人特別脆弱,別人有事不打緊,妳出事就會特別危險」
我楞楞地望 他,倒抽一口冷氣。
***
檢驗報告果然是血鈣太低。於是專家替我調整服藥的份量。當時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檢查,大致無礙,便安心下去。
這下以為很快可以走上康復之途了,可是奇怪得很,日子一天天過去,血鈣還是偏低,身體還是一點力氣都沒有。
***
專家說:忍耐一點吧,慢慢會調整起來的。
然而就在那時候,另一位專家出現了,掀起戲劇性的另一幕。
這是一位好朋友,也是醫生,美國某知名大學的生理學家。他剛回台灣度假,看我病得不成樣子,煞是焦急,終於想出一個方法,保證可以使我的血鈣迅速增高。他建議我們用骨頭熬湯,同時把鈣片放進湯 一起煮。我們照辦了。
那時候我服的鈣的份量已比平常多三倍,再加上骨頭湯的剌激,血鈣果然一下子猛升上去。可是,咳,沒想到升上去以後卻產生不可控制的悲劇!
起初大約有兩、三天的光景精神突然好了,竟自慶幸之際,卻無緣無故地嘔吐起來。嘔吐多半在早上發生,而且不斷加劇,吐得反胃,甚麼東西都吃不下,苦不堪言。
那段日子真是又凌亂又可怕,發生過的事情都記不清先後次序了。只記得那一天吐得特別凶,整天不能吃東西,混身不對勁,到了晚上,伯母看我不對勁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和伯伯商量之下,決定還是把那位相熟的大夫請來。大夫總算有人情味,破例摸黑出診一趟。
還記得大夫一把脈,眉頭皺起來,用血壓計一量,臉色都變了,再量一遍,嘴角抽搐 ,兩隻手顫巍巍地把血壓計放下,別過身去對伯母用受了驚的聲音低喊:
「把她送到醫院去把她送到醫院去」
始終沒有問他當時我的血壓高到怎麼樣的地步,不過肯定情況是相當可怖的。
大夫在極度無助中還是替我打一口針─大概是鹽水或者葡萄糖之類,補充一下體力;又或許是鎮靜性質的,總之當天晚上算是平靜地度過了。
第二天清早,伯母馬上打點把我送去看另外一位西醫,和他商量入院的事。
***
醫院 面的護士小姐像大夫一樣吃驚─雖然經過打針之後,相信我的血壓已經不像前一晚高得那樣可怖。不過180度的血壓仍是令人憂慮的,何況眼前這個還是年輕的病人,身軀瘦瘦小小,臉色黃中帶青,沒有一絲血壓高的 象。
「妳再量量看,我怕量得不準。」護士小姐推了她女伴一把,看看我,又看看血壓計。
另外那位護士又量了一遍,結果還是一樣。早上醫生量是140 度,幾小時之內升了40度,而前一個晚上恐怕是超過了200度。三個月前曾因血壓過低而昏厥過去,現在休養了三個月,滿以為快要恢復正常之際,卻因血壓過高而給送進醫院來了。
誰知道我體內的化學元素在搞甚麼名堂?這趟不可能是血鈣過低了,說不定是過高了吧。
驗血的結果證實了這推測不錯。
這以後的事情都記不清楚了,反正是一片混亂,猶如創世以前的混沌黑暗。
在混亂當中只有一個清楚的決定。我應該回香港的家去醫病,不能再拖累張伯伯、伯母。剛好家 來信說有位朋友日內將赴台,請他護送我回去。
從醫院出來那天染上了流行性感冒。發燒又加上胃部發炎,除了米湯,根本不能吃甚麼東西。荏弱的身體更荏弱,再加上鈣的不穩定,整天嘔吐,全身都不對勁。那些日子不易熬,卻還要打點行裝返港。
記得返港前兩天幾位最知心的朋友來道別,我苦笑對他們說:「我快要像約伯那樣咒詛我的生辰了!」可幸我的朋友不是「約伯的朋友」;他們從沈默或簡單的話語所傳遞無限的同情、慰藉與鼓舞,使我焦渴的心靈得到滋潤。
一個多月前,我勇敢地發表了〈只有祝福〉一文,現在信心馬上受到考驗和挑戰。其實當時我還看不到日後會有更大、更重的試煉。
上飛機前醫生替我做好安排,向航空公司申請了輪椅,讓我坐在輪椅上,給抬上飛機去。當時的我,因為不能進食,混身無力,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不過靠 大夫給我打的針藥,仍然維持 體內需要的營養,而且臉色比平常更好,坐在輪椅上,表面看來還是一副精神奕奕的樣子。我一直對大夫那些神奇的「補針」訝異不已。
於是我坐 輪椅降落香港 德機場,迎向家人又焦慮又寬慰的懷抱。回到家門的時候,他們預備了另一張大籐椅,讓我坐在上面,由兩位強壯而熱心的友人抬上四層樓去。
這一切的發生比戲劇更戲劇化,然而所有的興奮使我體內不穩定的情況更惡化。日後回想,其實當時的情況危險到極點,而且沒有一個人知道該怎麼辦。家人預約好的一位有名內科醫生度假去了,還得等一、兩天才回來。而當時那些「神奇的針藥」效用過去之後,我完全垮下來了。
***
家人把我送入醫院的時候,身體似乎一無是處。鈣的份量高得驚人,血壓高至200多度,而心臟、腎臟、血液都不正常。不久我就陷入半昏迷狀態,幾日幾夜浮沈在混沌幽暗的深淵家人看 我痛苦不安地輾轉反側,聽 我呻吟,說囈語,冰涼的恐懼漫過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醒過來。
咳,在生死線上,受 割裂之苦的往往不是病人,而是那些愛他們的人,那些眼睜睜無助地看 他們在生死邊緣上輾轉的人。
不過我終於從生死邊緣滾回來了,雖是極度虛弱和不平衡,但終究也脫離了危險。
在那位醫術高明的內科醫生悉心調理下,我的病情日見進步,鈣的成分也逐漸平衡過來。
還記得第一次重新吃米飯那種感覺。多久沒吃米飯了,多久沒嚐過吃東西的樂趣了;當我捧 那一小碗母親親自煮的牛肉飯,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感謝和幸福充塞喉間。
然而正當一般健康情況在復原之際,醫生帶來了一個消息:從肺部的X光片發現有一些暫時未能判斷的陰影。這個消息雖然 我有點兒煩惱,但接 的日子精神和胃口一天一天好起來,我也就不以為意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我從酣睡中給醫生喚醒。我的主治醫師帶了另一位外科醫生來。
「我想請X醫生摸摸妳脖子底下的淋巴腺,就是我前天替妳摸過的地方。」
外科醫生動作敏捷地摸了兩把,然後對主治醫師頷首。
「我們發現妳有一、兩顆淋巴腺脹大了,可能要替妳動個小手術─最小的手術─拿出來化驗,看看和妳肺部的陰影有沒有關係。」主治醫師說 ,不敢直視我。雖然他裝出了笑容,卻掩飾不住侷促。
我楞住了。
***
在台北看內分泌專家的時候,曾經要求他給我作徹底的檢查:「大夫、朋友都勸我到榮民總醫院好好檢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癌症復發,因為有這許多奇奇怪怪的症狀」
「我已經告訴過妳這些都是鈣不平衡的症狀,一旦恢復正常,這些症狀也會慢慢消失的。」專家頓了一頓:「不過要是妳不放心,入院檢查也是可以的,只是很不容易找到 位,妳也知道的。我們試試看吧,我給妳寫張單子。」
專家一面寫 單子,一面接 說:
「問題是妳要檢查是否是癌,得先停掉甲狀腺藥一段時間;在妳目前的情況,恐怕對妳也不好。依我看,目前並無癌症復發的徵狀。」
「既然您認為可能性不大,那我也懶得去檢查了。其實我自己並不擔心,只是一些朋友─」接 我又加上一句:「那麼到底甚麼是癌復發的徵狀呢?」
「淋巴腺腫起來。」專家止住了筆,把單子撕掉。
***
他那句話還在我腦海躍動,現在主治醫師告訴我說發現有淋巴腺脹大了!我楞楞地盯住他。
「不一定有甚麼問題的,」主治醫師忙加上一句:「只是那麼多年沒作檢查,總應該作個大檢查了。這只是例行公事吧了。」
我把頭髮向後一撥,強裝出勇敢的微笑。
「好吧。」心 卻涼了大半截。
「反正不急,總得等妳的鈣恢復正常才說。」主治醫師又說:「不過從今天早上開始,我們已把妳的甲狀腺藥停掉,因為過一段時期須用放射性儀器做一個特別測驗。」
「把甲狀腺藥停掉,做一個特別測驗,那就是看是不是癌了。」我的反應很快。
「那只是萬分之一的可能性而已,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主治醫師用盡了醫生的技巧來安慰我。
於是展開了病的第三個回合。這一展開,使得前面兩個回合完全失色。
***
睡意全消,我靜靜躺 想心事。假如我去世,喪事禮拜的儀式該怎麼樣?假如可能的話,一切務必簡單、優雅;我希望葬在小妹妹旁邊。
無論如何,就在那海天一隅的大花園 ,那個從小女孩時代就愛去徜徉的地方。
唯一的話題是怎樣處理我唯一的「財產」─ 我的日記和信件。燒燬抑存留?
父母親送了晚飯來。吃了兩口,胸際有甚麼塞 似的。勉強再吃兩口,放下來。
「怎麼沒胃口?前幾天不是吃得好好的?」母親的眼尖得很。
「今天停掉了甲狀腺藥,可能影響了胃口。醫生說要做試驗。」不敢馬上把施小手術的事說出來。
「這種甲狀腺藥怎麼反應那末快,才停掉就影響胃口」母親的眼色露出疑慮。
我支吾 。
他們離去的時候,我依戀地看 他們的背影。
(恐怕沒有太多機會了!)
薄暮時分,妹妹來了,她要往海外深造,來跟我話別。我們走到外面的小園子去散步。我們坐在矮小的竹樹下禱告。
她哭了,我沒有掉眼淚,心 卻說 :「別了,我們在天家再見吧。」
晚上展開信箋,寫了一封信給台北的幾個知己朋友。
(這一切都必須馬上做妥,否則病況瞬息轉變,再沒有機會說我要說的話了。)
「我唯一的願望,」我寫 :「就是: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書〉1:20)」
(他們幾位看到信,大驚失色,以為我性命就在旦夕之間。)
當天晚上,一夜沒睡好。整個人浮沈於一種彷彿沒有時空的「時間」和「空間」中。似乎停止了思想,卻輾轉反側;似乎反覆思想,卻又沒有留下思想的痕跡。
癌的恐懼竟在有意識與潛意識中滲透了每個細胞。
我嘗試分析到底自己恐懼的是甚麼?
我知道我不畏懼死亡:因為雖然談不上「成就」,但我已獻出凡我所有,過了充實有意義的一生。
我知道我不畏懼死亡:因為我是一個蒙赦免、蒙救贖的人;死亡於我並非「不可知之地」,而是遷移到一個更美好、更光明的地方,更有能力地獻上自己。
那麼,我恐懼的到底是甚麼?
─那通往死亡之路:那陰翳的淵谷、冰冷的河流。
─死亡之前的痛苦:那蠶食人肉體、心靈的煎熬,那時日的耽延
─治療期間的折磨以及所有必須忍受的不便。
─家人的焦慮以及會帶給他們的拖累。
─所有與癌有關的聯想
我畢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畢竟還是脆弱的。
體內的鈣降得十分慢,因此動手術的日期耽延 ,另外要做的特別試驗又未開始。我的健康情況卻一天一天有進步。
在懸 許多大問號的同時,我在醫院 過 平靜的日子,在學習以前從未學習過的功課。
當然,醫院 的日子,無論表面如何平靜,底下總是醞釀動盪、不安,和各種悲劇的。對面病室住 一個中年男子,已進入肝癌後期,天天靠打嗎啡止痛。可能所有的止痛藥用多了都會失效,又可能有別的原因,醫生囑咐護士不能給他注射多過某份量,可憐的病人,在痛苦難當的時候,追在護士小姐後面,乞求她們給他多打一針。護士小姐匆匆逃避,或哄他,或罵他,就是不能答應他的要求。噫,那麼多年來我總拂不掉那幅悲慘的圖畫:那滿佈血絲的眼睛、抽搐的臉、淒厲的呼求、絕望的追逐
這就是醫院生活。醫院不是一個鳥語花香的地方;醫院佈滿了埋伏 的危機、計時炸彈、慘不忍睹的景象、令人心酸落淚的事件。
在等候真相揭露期間的一個晚上,我不小心把桌上的杯子砸破了,滿地都是玻璃碎片。
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工進來,默默地把地上的殘局收拾好。
「這兒,一點點,給妳的。」我塞給她五塊錢小費。(那時候廉政公署還沒成立,一般醫院的規矩還接受小費。)
「不,」她輕輕地把我的手推開。「我跟妳不熟,沒服侍過妳,不該要這個錢。」
她的視線落在我 几上的《聖經》。
「妳也是信主的?」
我點點頭。「妳也是?」我們就這樣聊起來。
「小姐,上帝在我的身上的恩典太多了。我的雙腿就是祂醫好的。醫生說已經沒有希望,我躺在醫院 動也不能動,只有禱告。 會的弟兄姊妹也為我禱告。然後我昏迷了三天,醒過來就好了。也不用開刀。我昏迷過去,就像給人家打了麻醉針」她愈講愈起勁。
「我今年六十多歲了,身體還是這麼健壯。」我原來沒想到她有這麼大的年紀,仔細端詳,眼角的皺紋果然不少,眼睛瞇成一條線,好像視力不大好,可是皮膚卻很光潤。「我無論做甚麼事都是為上帝而做,每天東奔西跑也不覺得疲倦。我當的是夜班,白天只睡幾個小時,其餘時間都是為上帝工作。我書讀得少,沒甚麼學問,不會做大事,可是我天天為病人禱告,上帝也聽我的禱告,輪到我當值的那個病房,病人都睡得安安穩穩,一夜平安無事。」
「小姐,我們來做個禱告,好嗎?」她一手把房門關緊,站在我 邊,挺自然地為我禱告。
朦朧的燈光下,白衫黑褲的身影,站在我 頭為我的病禱告。這情景真美,連續幾個晚上,我關上燈就感覺她站在我 邊。我深信這老嫗單純的信心更易達到上帝的寶座前。
我又深信這位老嫗對病人的確會有她的貢獻,尤其對一般貧苦大眾。所謂知識分子平日口 講得硬,科學、哲學、神學、心理學「一大堆書包亂拋」,可是在病魔纏繞,肉體、精神都不舒適的時候,一切理論都變得毫無意義。病人所需要知道和經驗的是一位能實在臨到他們的神、一位慈愛的天父、一位隨時隨地聽他們禱告、安慰他們、又有能力醫治他們的主。
***
當我從醫生洩露了的「口風」中,發現癌的可能性愈來愈大的時候,竟有一股勇氣使我挺身起來迎向它:
癌真是那麼可怕嗎?癌不會比戰爭、暴亂、飛機劫持更可怕,比兇狠的謀殺、殘暴的酷刑、無人性的屠殺、洗腦
死亡之路也真是那麼可怕嗎?多少先聖先賢都憑 信心通過那條路去了。我豈不可以跟 詩人大 唱道:「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與我同在。 的杖、 的竿,都安慰我。」
那首孩童時代在主日學唱的聖詩,突然變得非常實在: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假如我還存 懼怕,只是因為我對上帝的愛還認識得不夠透徹,正如「愛的使徒」約翰所寫的:
「上帝就是愛,住在愛 面的,就是住在上帝 面,上帝也住在他 面。愛 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翰壹書〉4:16-18)
上帝固然是我們看不見、摸不到的,然而上帝的愛藉 屬祂的 體具體表現出來。從世界各地,我不斷收到許多來信:
「在台灣的同工、同學們迫切地為你禱告。」
「我們在洛杉機的弟兄姊妹不斷地記念 你。」
「在新加坡的各個不同團契的禱告會中,常常為你代禱,有許多人是你根本不認識的。」
有在加拿大,在菲律賓,遠自紐西蘭的。
**
每天有數不清的禱告為我獻在壇上(這個思想簡直可以 我全身燃燒起來),有這許多人為我禱告,可以隨時期待各種神蹟的出現;有這許多人為我禱告,沒有甚麼是可怕的─無論甚麼事情發生都不會是可怕的。
在初期震盪過後,繼之而來的是對死亡消極的嚮往。在一個如此動盪不安的世界,一個人性愈來愈湮沒的年代,以自己如此荏弱的身軀,死亡未嘗不是好的。況且死亡可以解決自己所不願面對的問題。
可是每當這個思想出現,我總會羞慚起來。我知道只要我被這種思想籠罩,死亡不會臨到我,因為那是對生命的不忠。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死亡會臨到。或許直到有一天,我從靈魂深處呼喊:我要活下去!為上帝活下去,為愛我的人活下去!縱然要忍受折磨、痛苦及各種威脅,我願意接受考驗、正視問題。
(哦!讓我們不要去查詢、追究痛苦的來源與根由,這是超出我們的範圍。讓我們拾取一點古希臘人的智慧。我們所需要的是正視痛苦的勇氣、忍受痛苦的力量、在痛苦中獲得的安慰與鼓舞、從痛苦中所產生的善良的果子。)
小手術動過了,報告還沒有發下來,卻先輪到做那個特別的試驗。
是放射同位素試驗。那是當時比較新的醫學方法,據說對癌症的診斷最為準確。全香港一共也沒幾部這種機器,我當時養病的醫院沒有,因此要回到我以前第一次入院的公立醫院去。這是我離開香港後第一次回到那家醫院,以前在放射治療部遇到的那位醫生已晉升為專家。
這個試驗一共要做三天。到了第三天,我怯怯地問那位技術員:「今天可以知道結果了吧。」
她遲疑了一下:「差不多了,待會兒妳去見醫生,他會告訴妳的。」然後她以更親切、溫柔的語調問我:「妳自己覺得怎樣?有沒有甚麼不舒服?」
從她的語調我馬上猜到了結果。
「醫生,我希望知道結果。」我驚訝於自己的平靜。
「嗯嗯」那位放射治療專家慢吞吞地回答:「是有這種情形。不過可幸妳這個癌發展得非常慢,而目前妳還能吸收碘。它蔓延到肺部可能也好幾年了,不過只要我們能控制它,使它不致蔓延到別的地方,妳還可以活很久,八年、十年、或甚至十多年誰曉得」
接 他又解釋:「妳這種癌是甲狀腺癌中最溫和的一種。」
他頓了一下,嚴肅與詼諧的表情交織 在他臉上掠過:「假如我也一定要有的話,我就挑妳這種。」
手術報告發下來了,淋巴腺橫切片化驗的結果是「肯定的」。現實擺在眼前,過去的診斷沒有錯誤,現在的診斷更多方面證實沒有錯誤。
──
蘇恩佩,70年代「突破運動」(基督徒文化更新運動)發起人之一,創辦《突破雜誌》。年輕時已罹患甲狀腺癌,之後一直與病魔糾纏,同時委身文化使命,以自己的生命回應社會,回應信仰,於1982離世。著有《死亡,別狂傲》、《蘇恩佩文集》一、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