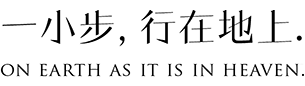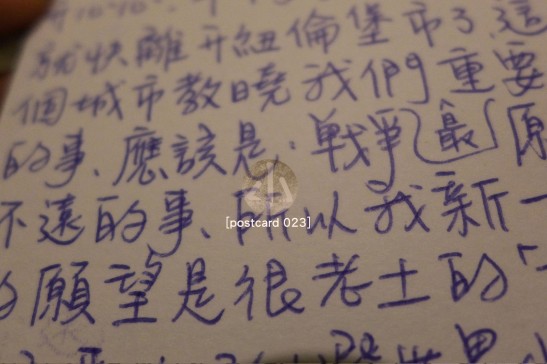你的新年願望是什麼?
如果我說……我的新年願望是世界和平,那會不會太矯情,或是太像要參選世界小姐?
但,那是我真實的願望。
坦白說,我們這些住在和平地區的現代人早已對戰爭的消息感到麻木。我們清楚知道世界上,仍有人天天在槍林彈雨下掙扎;我們甚至不時從電視、從網路看到新聞片段──只是我們都不覺得震撼。
也許是因為無力,也許是單純看得太多戰爭電影,玩得太多模擬戰爭遊戲,把一切都麻木、抽離了。
頹垣敗瓦?哦。呼天搶地?哦哦。唔。
或許,唯有「親歷」戰爭現場,才能叫人重新醒過來。
***
戰爭就是 一切灰飛煙滅
談起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兩個從沒有好好讀歷史的人,是自從在紐倫堡住下來,才知道這裏在二戰期間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這3個月,來回於舊城區,參觀了各種博物館,在不同的遺址慢走,我們發覺,這個城市正用盡不同的方法警告我們:戰爭是很容易發生的,我們絕對不可以重蹈覆轍!
紐倫堡舊城區的最高點是皇帝堡(Kaiserburg)。在羅馬帝國時期,它是羅馬皇的其中一座行宮。現在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遊客到這裏來看二千年前的皇宮。
在城堡範圍中央,有一座高塔,只要爬上去就能看見城市360度的全景。在一個9月的陰天,我們和奶奶一起爬到塔頂,想要欣賞一覽無遺的景色。我驚訝的發現,在圓塔的每一個小窗戶旁邊,都有一幅黑白照片,記錄了差不多70年前,從這個角度看出去,舊城被盟軍炸得一片頹垣敗瓦的景象。
這是從高處看下去的舊城區。
那條我們常常閒逛,朝城堡拾級而上的小街,堆滿了大石,兩旁精緻的小屋被移平了;那幢宏偉的St Sebald教堂,差點認不出來,只剩下木支架,高塔都倒下了;我們很喜歡參觀,文藝復興畫家Albrecht Dürer的小屋竟然奇蹟的絲毫無損,但它附近變成一片爛地,對面的屋子,就是我們買兔子明信片的小店,是ground zero了……
腦袋開始混亂,那間小店,在那個時空根本不存在。
但就是因為時空交錯,因為對這些街道小店的熟悉,留下過快樂回憶,看着黑白的對照,才覺得震撼,才覺得心裏有點隱隱作痛。
在高塔的圓窗,我重覆看着這些照片,突然覺得它們不僅來自過去,也可以是來自未來──如果,有一天戰爭來到,眼前的一切就會再次灰飛煙滅,一切也成為空白。
戰爭就是 一剎那的敵我之分
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崇尚理性的德國人,竟然可以失去理智的屠殺猶太人,可以不顧一切的侵害旁邊的國家。在紐倫堡市區的一角,在平靜的Dutzenteich湖旁,有一座「文獻中心」(Nuremberg Documentation Centre),詳細記錄了人們如何集體墮入這個黑暗的漩渦。
紐倫堡是納粹主義propaganda的中心,這裏每年都舉辦大型的納粹巡遊,一方面向世界展示國家實力,另一方面也大灑金錢麻醉民眾,讓人民在吃吃喝喝當中,相信納粹主義帶來的是豐足,是民族自豪,是榮譽。在文獻中心,會看到當時的電視短片,看見人們怎樣在納粹旗下大吃大喝,怎樣對希特拉的來臨歡呼尖叫。(有關於納粹巡遊的遺址,可看Postcard015)
與此同時,納粹黨正一步一步的趕絕猶太人。先是叫大家杯葛他們的店舖;再來是要他們把自己標籤,在衣服上掛上猶太星;接着是強迫他們離開家園,搬進一個個集中營。為了叫這些明顯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得到民眾支持,納粹黨不斷在各種平台抹黑猶太人:他們被推諉為掠奪德國人經濟成果的盜賊,他們是低等的種族,他們是來侵佔我們的土地,他們不配成為我們的一份子……一直滾下去,最終是,他們是死有餘辜的。
這是當年把社會上的「低等族羣」標籤的圖表,政治犯、猶太人、厭惡性行業、同性戀者等……全都要自己標籤。
不足10年時間,一方面高舉自己族群的優越性,一方面煽動羣眾中的敵我之分,最終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戰中,300萬猶太人的死亡。推出謠言,把謊話說100篇,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歸咎於這羣「敵人」,無限量放大他們的不足……就能叫人把自己的冷血,變得合理化。
因為敵人都不再是人。
每次我讀到這段歷史,我都會感到一陣腦麻痺。我仍然不太能接受或消化這段可怕的歷史。最近,我還會想起香港。我們在撕裂,我們在互相抹黑,把對方描繪成不是人,指責他們為「非我族類」,無論是城邦派與社運派之爭,「香港人」與「新移民」之間的「仇恨」。我不是說,這一切都是非理性,當中都有要處理的分歧,有各種不可忽視的緣由。然而,我害怕的是,當我們把「非我族類」標籤,把他們都扭曲簡化為「蝗蟲」、「左膠」,我們同時是在扭曲自己,也叫自己的盲點慢慢擴大,墮入那一剎那的敵我之分,甚至蔓延為全城的瘋狂。
我最害怕的是,瘋狂以後,暴力就會隨之以來。
和平就是 你與我之間的共同責任
紐倫堡在二次大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位置。當一切完結,當德國納粹黨戰敗,盟軍決心不讓這件可怕的事重演。他們可以選擇一如既往,處決或囚禁戰犯,來懲處這批冷血的戰犯,恐嚇或制裁德國。
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選擇了開展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庭──「紐倫堡大審判」(Nuremberg Trials)。在1945年11月,在美國的佔據地紐倫堡市,在Court Room 600(法庭600)的犯人欄,坐着23名納粹戰犯,當中包括希特拉指定的接班人Hermann Goering。檢察官和法官都是來自4個盟軍國家:美國、法國、英國和俄羅斯。
現在的Court Room 600偶然會開放給公眾參觀。在公眾席,有三個小熒幕,只要把它扭向犯人欄、法官席、證人欄或是檢察官講台,就可以重看當年的黑白片段。我們把它推向犯人欄,熒幕隨即播放這些納粹高層進入法庭的片段。他們形神輕鬆,互相說早安、握手、坐下,Goering戴着太陽眼鏡,一臉平靜……那一刻,我腦海一片空白。
怎麼可能對着這批敵人,而仍然保持公平理性?
我和猴子坐在公眾席上,相對無言。
剛巧這時有一位美國歷史學者,走進Court Room,向他的歷史團講述這個紐倫堡大審判的重要性。「活在今天,你可能覺得,戰犯接受國際法庭審判是理所當然的事,No big deal。但70年前,卻不是這樣。當時的國際社會根本沒有共通的法例,一個國家在自己領土內所做的惡行,其他人無權插手。坐在犯人欄的23個戰犯當時神態自若,很有信心,自己能獲輕判。老實說,這是史上第一次國際法庭,怎麼可能成功?」
「想像你是當時的檢察官,你眼看像Goering這些極其聰明的納粹官員坐在犯人欄,即使他們的罪行路人皆見,但仍有機會在尚未健全的國際法中逃去。你的壓力有多大?萬一這羣殘殺平民的高官罪犯能輕鬆過關,世界還不會大亂嗎?」那位美國歷史學者說。
「然而,我們卻絕不能以同樣殘忍的手段對待他們。否則這只會造成更長遠的後果,讓極端主義延續下去。這是為什麼,當時盟國,特別是美、英、法,堅持要公平和公開的審判。」
美國的檢察官Robert H Jackson在開庭之日,說了一篇長達幾小時的演說,是20世紀其中一篇最精彩的演辭(詳細內容)。我回家找出來看,其中開首的幾段,已是相當震撼:
“The wrongs which we seek to condemn and punish have been so calculated, so malignant, and so devastating, that civilization cannot tolerate their being ignored, because it cannot survive their being repeated. That four great nations, flushed with victory and stung with injury stay the hand of vengeance and voluntarily submit their captive enemies to the judgment of the law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ributes that Power has ever paid to Reason.”
由這個審判起,國家之間明白,我們不能只靠「拳頭」、「武力」(Power)來維持秩序,亦不能各家自掃門前雪。一個國家的瘋狂,能掀起整個世界的禍害。我們要用「理性」(Reason)來維持世界和平,阻止像二次大戰一樣的事情再發生。面對這班殺人如麻的敵人,縱然我們很想報復,仍要堅持不用武力,先放下仇恨,要用公平的審訊來制裁他們。
“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the record on which we judge these defendants today is the record on which history will judge us tomorrow. To pass these defendants a poisoned chalice is to put it to our own lips as well. We must summon such detachment and intellectual integrity to our task that this Trial will commend itself to posterity as fulfilling humanity’s aspirations to do justice.”
而且,我們絕對要記住,今天用什麼準則審判懲處他們,明天同樣的準則也會放在我們身上。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只有當大家也共同維護這些準則,世界才有和平。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感到很震撼很感動,似乎還未完全消化到,但就是常常想起這些片段。也想起敍利亞,想起阿富汗,想起蘇丹……
我只知道,維護世界和平不只是超人的責任,而是在於每個人都不再閉起眼睛,願意共同承擔。戰爭的緣起,可能真的只是一個人的瘋狂,但最後蔓延全球,卻是全球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新一年,希望自己更關心世界,希望世界更和平。
關於Postcard 023:
紐倫堡還有一個地方,我常常記着,就是舊城旁的St Sebald教堂。這間教堂長期有一個關於和平的展覽,展出這座宏偉的歌德教堂在二戰後,被炸得一片頹坦的模樣。「我們真的要重建嗎?似乎把整座教堂鏟平更明智。」「但市民決意不讓上帝的殿空着。」展覽記錄了人們怎樣維修教堂,當新的教堂鐘再次裝上,那一夜全城慶祝。2013年的平安夜,我們到St Sebald上崇拜,清脆的鐘聲迴盪整個舊城區。
我在教堂裏買了兩張Postcard,一張是畫家筆下的浪漫雪景,另一張是二戰前後的對比。我把畫家筆下的Postcard寄給Ed兄,因為他是唯一會陪我去看「難民電影節」這類節目,或是在香港電影節一起看一套關於中東紛爭的阿拉伯電影的朋友。哈哈哈……希望回來後,你還是會繼續陪我去看電影,一起關心世界。
–
Dydy,29歲,前Breakazine!編輯,為人膽小騰雞,卻心郁郁想認識世界。2013年急急搭上了工作假期的尾班車,與外子(又名猴子)開始一年的外地生活,離開之前已決定每個星期寫一張postcard回來香港給一個掛念的人。
dydy_sezto@yahoo.com.hk
Breakazine!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breakazine